杨国荣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伦理学与实践智慧
付长珍(以下简称为“付”):杨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对重大项目“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中国重建”的支持。能否请您谈谈伦理学与实践智慧的关系?
杨国荣(以下简称为“杨”):“实践智慧”所涵盖的面比较广。当然,伦理学是实践学科,通常讲的实践哲学也包括伦理学,“实践智慧”则是其题中应有之意。我在《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中已提到,实践智慧的基本特点在于把普遍和个别沟通起来。实践智慧包含普遍原则,而“原则”是涵盖万有的,不可能兼顾任何一种特定的情境,人的实践则展开于一个个特定的情境之中,如何把普遍的规范或原则与具体情境中的行动沟通起来?这是“实践智慧”所面对的关键问题。这里重要的是我所说的“存乎其人”,因为没有一般的程序或形式可以完全左右这一过程。实践智慧的特点就在于它不能完全被程式化或形式化。所谓“存乎其人”,主要指通过行动者自身的综合能力,将相关方面沟通起来。仅仅强调普遍原理或仅仅着眼于特定情境,都无法实现结合。真正要把这两者沟通起来,还需依靠具体的实践者或行动者。对道德领域来说,实践者也就是道德主体:正是道德主体,将普遍原则与具体情境沟通起来。按照形式主义的观点,这一过程好像缺乏确定性:形式主义喜欢程序化、有规有矩地展开相关活动。但在实践智慧的层面,恐怕很难做到这一点。实践智慧在某种情况下与实践推理有相通之处:实践推理和逻辑推理不同,逻辑推理通常以归纳为方式,或者运用演绎的方式,前者表现为从个别到一般的推论,后者则是从一般到个别的进展。尽管方式不同,但都具有程序化的特点。实践推理则与之不一样,它首先需要确定行为的目的,然后选择恰当的手段、环节,以通过这一过程来达到相关目的,在这一意义上,实践智慧与实践推理确有某种一致之处。当然,相较于实践推理,实践智慧的面更广一些,作为逻辑推理的引申,它不仅限于某一领域。此外,非程序化也在逻辑上带来了不容易把握的特点,从而对实践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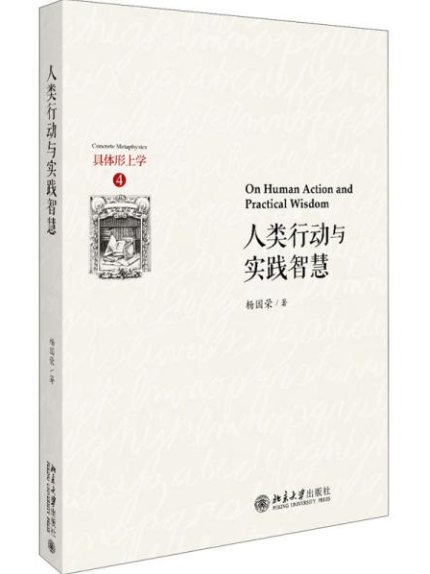
《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 杨国荣/著
(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付:如果聚焦德性与实践智慧,那么是不是可以更好地沟通中西伦理学资源?
杨:德性与实践智慧无疑有相互关联的一面,德性在于“成乎其人”,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将成就人作为重要之点,肯定的是首先需要塑造完美的品格,以此担保人的所作所为合乎道德;规范伦理则重视成就行为,具体关注行为怎么样展开、以什么规范加以引导,等等。在此意义上,德性伦理与实践智慧确有相关性。至于德性伦理如何把中西沟通起来,我觉得这里可能要具体分析。从德性伦理角度来说,中西方都有相关思想,并非只有中国伦理注重德性。在现在的西方哲学中,斯洛特(Michael Slote)讲情感和德性,麦金泰尔(Alasdair Chalmers MacIntyre)要求回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也都表现出注重德性的意向。可见,在西方思想中,也存在肯定德性的传统。从中国的主流倾向来看,重视培养人的德性构成了其重要特点,从早期的儒学到宋明儒学都体现了这一点。儒学中当然也存在区分,比较而言,陆王心学更注重尊德性、程朱则同时兼顾道问学,后者对知识进路较为注重。但总体上,这两者并非截然相对,即便程朱一系的伦理学对于德性也是予以肯定或认同的。所以,仅仅从德性理论与规范伦理的分别来区分东西方,可能存在困难。问题不在于中国伦理讲德性,西方伦理不讲德性,更需注意的可能是所注重的“德性”蕴含何种差异。事实上,即使在中国哲学中,对“德性”的理解也各异,如陆王一系和程朱一系便并不一样。我在《伦理与存在》中也曾提到德性和规范的关系,这确实是伦理学中一个比较恒久且绕不开的问题。从历史上看,哲学家或伦理学家各执一端,有的讲规范、有的重德性;从理论形态来看,德性最早与传说中的完美人格(如古希腊的英雄、中国的圣人)相关,他们都被赋予完美的德性。这种德性在凝结之后,进一步抽象化,便可把其中体现的德性提升为普遍的规范。也就是说,“德性”由此取得了普遍规范的意义。再进一步,则又需要将这种一般规范具体落实到一个一个的个体之上,使之内化为人的德性。这里既存在着互动,又表现为理论的某种“循环”。我们可以看到,从起源来说,德性和规范无法相互分离:在德性抽象化为一般的规范、规范内化为一定德性的循环过程中,不难注意到这一点。
付:如果要在世界哲学的视域内思考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重构,那么就需要它既能体现中国性,又能体现时代性,关键是能否找到一个理论结合点呢?
杨:这也是一个问题,中国伦理学放在世界哲学的视域中,呈现什么样的品格?不同的文化传统及其哲学思想都有各自的特点,如何对此加以概括?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去做的一项工作。总体上,中西哲学都关注伦理、规范、理性、感性以及其他特性的一面,关键在于,如何具体把握其不同的趋向和意义。康德哲学对理性原则、规范给予了比较多的分梳;休谟(David Hume)区分了两种德性(“Artificial Virtue”与“Natural Virtue”),同时,对情感的关注更多,而情感也是构成德性的重要内容。中国哲学也是如此,刚刚提到陆王与程朱,都涉及德性与规范的问题。但是,具体的理解又有所不同。光靠一个抽象的德性概念去区分出中西的差异,可能并不容易。在比较中西思想时,人们常习惯于说中国如何、西方怎样,但其实每一种抽象概括背后都存在很多问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人讲“合”,西方人讲“分”,其实,我们也可以找到很多西方思想家讲“合”的例子,而中国哲学中如名家学派、朱熹也重“分”(所谓“铢分毫析”)。我个人不太倾向于做这种宏大叙事的概括,因为这无助于具体把握相关问题。
付:杨老师,您在和李泽厚先生的对谈中,特别提到伦理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厘清伦理和道德的分野,是否是伦理学研究的一个元问题?
杨:关于伦理与道德的关系,晚近一直存在争论,李泽厚便对这两者做了很细致的区分。从历史上看,中国伦理中“道德”不是“Morality”的意思,而是“道”和“德”两者的结合。“Morality”和“Ethics”这一意义上的道德与伦理,在中国传统中并没有很严格的区分。在西方,这一区分倒是很早就开始了。远的不说,近一点,康德(Immanuel Kant)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便各重一端:康德讲道德,黑格尔重伦理,两者的理解确实有分别。康德所讲的“道德”,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属于“当然”,康德推崇道德律令,侧重于“应当如何”;在黑格尔的视野中,“伦理”首先与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相关,这些都属现实的形态,在黑格尔以“伦理”为主题的背后,确可以看到对现实生活、人伦关系地注重。在这里,伦理和道德形成了如下区分:伦理意味着现实形态——伦理关系;道德则主要关涉作为当然的普遍规范。在晚近的中国哲学中,李泽厚也对两者做过区分。当然,我不太赞成他的看法。按我的理解,从历史上来讲,不论是在希腊语境还是拉丁文所表达的思想形态之中,道德和伦理之间都没有根本的分别。中国人很早就谈伦理,讲人伦关系。所谓人伦之理,首先就要承认人伦关系,这一点和黑格尔很相近:伦理就是人伦关系中的普遍原则。比较而言,“道德”这一概念相对宽泛一点,它与道家所讲的“道”和“德”有关联,“道”首先表现为形而上的存在原理,这一普遍之道内在于个体之中,或个体由“道”而有所得,便是“德”,这一关系的背后所体现的,是道德和现实生活并非完全无关。中国哲学认为“德”意味着“有诸己”,即普遍的原理为个体所把握,并内在于个体之中,就形成“德”。这一意义上的“道德”与现在所说的“Morality”尽管侧重不同,但有一定的相近之处。从历史上看,在西方话语中,道德与伦理一开始都与习俗、日常行为方式相关,二者没有严格区分,后来的哲学家们逐渐有所偏重,前述康德与黑格尔即是一例。黑格尔讲伦理,康德则重“道德”,后者的《道德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Morals)进一步将道德(Morality)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权利的学说(Doctrine of Right),一是德性的学说(Doctrine of Virtue),权利学说与法哲学相关,德性学说则侧重于伦理学。尽管作为中国传统概念的“道德”与“Morality”有某种相近之处,但中国人在“Morality”意义上讲道德,是比较晚近的,先秦很少直接以此说道德。
刘梁剑(以下简称为“刘”):杨老师的《伦理与存在》一开始也讨论了道德与伦理的区分,其中也引用了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关于二者的区分。
杨:我的著作的标题是“伦理与存在”,但后面的副标题则加上了“道德哲学研究”,从这方面看,我对两者也没有做很严格的区分。事实上,我在以上书中明确说,这两个词之间并没有特别严格的意义差异。威廉姆斯把苏格拉底(Sokrates)的“人应该如何生活”作为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他的一家之言。语言的特点是约定俗成,如果以某种方式去约定,则只要一以贯之,就可以如此运用。但是,不管讲伦理也好,道德也罢,实际上脱离不了伦理关系、道德行为的基本方面。也许从一般意义上讲,伦理更侧重于人伦之理,在中国人所说的人际关系或黑格尔所说的现实社会关系中,同时蕴含着制约行为的一般的理——伦理;道德则表现为对人的具体要求,并以“当然”的形态呈现。但考察伦理与道德,两者都不可完全偏废。同时,道德实践最后还是要回到人的生活之中来。康德重形式、先验,不大讲现实的东西,这是一种偏向;黑格尔固然较重现实的内容,但又是侧重于思辨意义上地注重。总之,我个人并不很倾向于对伦理与道德做很严格的区分。尽管我尊重历史上这些哲学家所做的区分,但是觉得这种区分的意义不大。

《伦理与存在》 杨国荣/著
(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付:现在学界有一种倾向,即把伦理学等同于道德哲学或道德理论。我想伦理学的研究不能化约为道德哲学所讨论的理论问题,特别想听听您的意见。
杨:我想这里还是要做一区分,即道德哲学或伦理学与道德家的分野。道德家侧重于颁布各种律令,这种形态近于宗教,如“摩西十诫”便带着宗教意味。伦理学与道德哲学则不以颁布律令为指向。历史地看,什么样的律令能成为道德律令,这不是某个人能够决定的,而是需要经历一个历史选择。中国人的“礼”为什么几千年来经久不衰?这与它在历史上所具有的维系社会秩序等作用无法区分,正是这种历史作用,使之慢慢被中国人所接受。这是历史选择的过程。当然,从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角度上讲,这种历史选择的过程包含着反思和辨析。从现实过程来说,道德律令的形成与接受离不开历史选择的过程,其中当然也包含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工作。从中国哲学的演化来看,早期儒家、宋明儒学以及现代新儒家,都在不断从各自的角度对相关的规范(包括“礼”)进行辩护、论证;根据西方传统,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拉图(Plato),一直到康德、黑格尔以至于现在〔包括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等〕,也从不同角度在做相近的工作。当然,伦理学家与道德家〔如摩西(Moses)〕不一样,他们不是去颁布某种规范系统,而更多地从理论的层面进行论证和讨论。伦理学、道德哲学的工作之一,是对已经存在的或者被历史所选择的规范进行理论上的辨析、解释。
刘:现在,学界有不少关于工夫论的讨论。工夫论的兴起是否意味着,伦理学及哲学除了理论运思的维度之外,还可以纳入生活方式的实践维度?
杨:一些学人,如倪培民,专门讨论工夫论,这也许有其学术价值,但我对工夫论持保留意见。在我看来,工夫哲学试图将具体的修行、修炼的方式,提升和扩展为涵盖万有的哲学形态,这恐怕存在理论上的问题。工夫确实有其哲学意义,但工夫哲学对工夫的观念泛化,则是我无法接受的。我在有关的讨论会上也表达了这一看法。
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域
付:杨老师,您的一系列论著贯穿着一个内在主题,即从“以道观之”到“以事观之”,再回到“以人观之”。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伦理学最本质的追问还是“人是什么”的问题。
杨:人禽之辨是个关键,其实质是追问“何为人”。康德四个问题的最后一个也关切“人是什么?”不管是哲学还是伦理学,都无法摆脱这个问题,伦理学则更集中地追问这个问题。
付:那如何体现伦理学和哲学其他领域的差异呢?
杨:这里涉及不同哲学领域,如本体论、美学、认识论,等等。本体论侧重于追问何物存在、如何存在等问题;美学关注对象的审美品格以及人的审美过程;认识论以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为指向。相对于以上学科,伦理学则主要以人自身的品格以及“如何做”为关注之点,包括如何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协调的关系,使社会形成一定的道德秩序。王阳明曾指出:“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在这里,“吾心良知”以德性为内容,对王阳明而言,德性的形成和人格的培养构成了出发点,但仅仅限于这一方面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后者意味着落实于社会人伦关系,由此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如果问伦理学追求什么,那么,简要而言:一是成就自己,使自我的内在德性臻于完善;另一是建立普遍的社会道德秩序。我们可以注意到,从“行”或“做”的层面,讲成己与成物和本体论、美学、认识论等具有不同的侧重之点。
付:所以,冯契先生的智慧说最后落脚到人的自由和真善美。

冯契(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杨:冯先生的真、善、美是接着康德讲的;人的自由是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比较注重的问题。事实上,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很早就把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我们可以看到,自由并不是西方近代启蒙哲学的专利。真、善、美的理想是近代以来康德哲学所追求的,中国哲学实质上同样如此。事实上,冯先生的思想也是试图整合中西方不同传统,包括马克思主义传统。现在也可以接着这一传统继续来讲,不必另起炉灶:“真、善、美”等本身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当然,在具体的价值层面,不同时代也可以赋予它们以新的内容,在世俗领域,与孟子所说的“可欲之谓善”一致,甚至可以将“吃得好些、穿得好些”的追求作为“善”的体现。总体上,真善美是人类在形而上层面所追求的价值;人类发展、演化最终要达到的理想是自由的不断实现。
刘:具体形上学有别于抽象形上学。与之类似,是不是也有具体伦理学和抽象伦理学的区分?康德那里特别讲形式化的一面。
杨:康德所重的是形式化的先验伦理学,黑格尔则试图回到现实,当然,他是在绝对精神思辨的框架底下回到“现实”,从而难以做到真正地走向现实。也就是说,尽管黑格尔对康德有很多批评,但他所追求的现实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实在,而是在思辨之下的一种存在形态。现在,显然无法继续这一进路,也就是说,不能将思辨的形态当成是现实形态。
刘:杨老师,您刚刚提到了人禽之辨,现在也有很多文章提到了“人机之辨”,认为我们现在讨论“人是什么”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新向度。
杨:现代科技发展很快,包括元宇宙、ChatGPT等,面对诸如此类的现象,有人欢欣鼓舞,也有人惶恐不安。在我看来,既不应盲目乐观,也不需要忧心忡忡。人类会走自己的路,这些东西的发展固然需要引导,但不会把人类毁掉。我是谨慎的乐观主义者。科技的发展,包括基因、克隆、人工智能等,这些都是人类走向自由过程中出现的插曲,要从这一角度去理解科技发展,而不能以可能要走向人类毁灭这一悲观心态去看。至于具体如何从哲学上去分析,我想现在还不是很成熟,要对此有一种哲学上的解析,为时尚早,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才起飞。”现在对科技进展议论纷纷、评论漫天,所谈东西都是大同小异,很多内容我不以为然。我在最近一篇关于如何走向具体世界的文章中,对“元宇宙”的表述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这一概念玄之又玄,有点夸大其词、故弄玄虚的意味。“Metaverse”之中“Meta”确仅有“元”的意思,但在汉语中“元”有在一切之前的意思,现在所说的“元宇宙”,其实是人的创造物,属于人化的世界,它的特点是虚拟实在与现实世界的沟通,作为现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的产物,并不是在一切人之外或超越于人的存在。“元宇宙”的提法容易给人一种误导,认为这是一种其大无外的原初存在形态。现在对很多现象常常过度渲染、人云亦云。当然,也不宜把这些东西一棍子打死。科技进步是人类自由的必要条件,是人类进步的成果和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对此,无须忧心忡忡。现在的一些论者往往喜作惊人之语,仿佛人类现在危机四伏、行将毁灭,似乎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所说的“超人”就要统治人类。这不是哗众取宠,就是杞人忧天。目前的论点之一是ChatGPT已经很智能了,以后进一步发展就不得了,小说、诗歌的创作都可以由其代劳。究竟如何发展,我们可以拭目以待。谈到小说这样的叙事形态,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写实一些的,莫言的作品过于魔幻,常抓住一些所谓“黑暗”的东西来怪里怪气地描述,我个人不太喜欢,当然,这也许是个人的审美趣味问题。以ChatGPT而言,其创作出来的东西,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原创性,ChatGPT本身是根据已有的数据展开的,如果没有人类积累的大量数据,它什么事也不能干:基于已有的数据,以最恰当的方式来组合,这是其工作的基本原理。然而,它们所依赖的数据是谁创造的?是人。ChatGPT没有原创性,原创强调的是从零到一,而从目前来看,人工智能还不能做到这一点。尽管有些人认为,人工智能,包括ChatGPT,具有学习能力,以后也许或有创造性,但原始的东西是人积累的,人工智能毕竟也是人设计出来的,是人设定的。从这个角度上讲,人的创造性还是不可替代的。超级计算机很厉害了,但从创造性的角度来说却不尽然。因为,超级计算机归根到底是人创造出来的。
付:它可以自学习。
杨:自学习的本领还是人教给它的,是程序安排的自主学习,自主学习必须依据已有的数据。ChatGPT就是个典型,它是个好学生,能很好地回答问题,但主要是依据已有的数据。
付:但它确实对伦理学的研究范式构成了强大挑战。伦理学是实践科学,必须能够回应现实、解释现实。
杨:伦理学有其基本的规定,这一方面不能丢掉,否则就没有本了。本立而道生。另一方面,像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等,确实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们可以基于现实的发展状况来分析,但在伦理学领域,做这种分析时,还是需要抓住传统哲学已注意到的“人之为人”等基本问题来考察。首先,一个前提性的事实是,人不同于物也不同于机器,机器是广义上的物。人不同于物的根本之点在于人是有自身内在价值的,康德讲“人是目的”,中国也讲“人为贵”。但是,ChatGPT这一类科技产品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工具,是为人所用的。需要把握这些基本之点,以应对千变万化的现象,否则容易闻风起舞、随物而变。传统儒学讲人禽之辨,肯定人不同于物,中国哲学虽然没有提出“人是目的”这一现代概念,但在实质上包含与之一致的观念,这里需要区分概念(名词)与观念。在马厩失火之时,孔子关心的是“伤人乎”,而“不问马”,因为马是工具,只有人是目的。如果在考察人禽之辨、人机之辨时,回到人与物的区分这一基本之点,便不会偏离正当的价值原则。
付:杨老师,您刚刚讲到人不同于物,人是有自身内在价值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觉得能够贯通起来。这也是中国哲学特别关注的,将“情”作为人机之际的一个分界。
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情”有两层意思,即情实之情与情感之情。尽管有些人认为,中国人在先秦时所讲的情都是情实之情,而非情感,但这是一偏之见,不合乎实际情况。事实上,即使在先秦,中国人所讲的情固然涉及情实之情,但也包含情感之情。荀子在《正名》中曾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这里的“情”,既有“情实”之意(表示“情”是性的真实内容),也有情感之意。情实与情感,并无绝对界限,中国人常将情视为最为真实的存在,这一意义上的“情”与情实之情具有内在关联。《性自命出》便指出:“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道始于情”之情,与庄子所说“道,有情有信”之意相近,侧重于“情实”;“情生于性”之情,则兼有情实与情感义。这一事实表明,“情”在中国哲学中常常具有沟通情实与情感之义。当然,在不同语境中,二者(情实或情感)可以有不同侧重。同样,情与性也彼此相通,《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肯定:“民有五性:喜、怒、欲、惧、忧也。”在此,情与性便呈现相关性:情构成了性的具体展开,真实之情即性。性、情相通,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情感与情实的相容。在中国哲学中,对于情感之情,有时不直接用“情”这一概念,但在具体情境中的运用,仍可以看到其实际所指为情,如恻隐之心,虽然没有提到“情”,但所指为情。在这里,我们需要从更为实在的角度来理解。对“情”地注重,也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注。同时,“情”与个体性具有更多关联,是内在于每个人之中的内在意识。理性可以是普遍的,但喜怒哀乐则每个人都不一样。
付:李泽厚特别强调“情理结构”“情本体”,力图凸显中国哲学的特质,又能回答普遍性的哲学问题。

李泽厚(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杨:李泽厚在很多地方都凸显出一种诗人的直觉。但关于情感这个问题,我觉得李泽厚的讨论并不很成功。他尽管讲情感,但主要还是从理性的层面来讲情。康德不讲情,把它当作经验的东西,这似乎更直截了当。康德固然也肯定对法则的敬重之情,但这种情更多地包含理性的内涵。李泽厚试图把情纳入进来,然而,他所理解的情感,也是受理性制约的情,在所谓“情本体”说中,李泽厚一再强调这一点。可以说,他对“情”是欲迎还拒,对“理”则是欲拒还迎。总体上,李泽厚并没有离开康德主义的立场。在西方传统中,休谟比较突出“情”。在其《人性论》中,休谟大谈情感,几乎将所有东西都放在情之下。当然,休谟对情的理解不同于李泽厚。休谟所讲的,主要是与理性相对的情,李泽厚所讲的,则是理性化的情。不能被两者表面相近的词语所迷惑。李泽厚后来尽管对休谟有所肯定,但骨子里还是注重康德的理性。撇开李泽厚的特定进路,确认情理的统一,可以此作为重要的思路考察中国伦理学的特点。事实上,中国哲学家与西方哲学家一样,既兼顾情理,又各有侧重。就早期先秦儒学而言,孟子一方面说“先立乎大者”“心之官则思”,一方面又讲“恻隐之心”,情与理这两方面都兼而有之。到了宋明时期,不同学派则各有侧重。张载、二程、朱熹都是如此。一方面,不能说理学完全忽略情;另一方面,理学又一再推崇天理。王阳明的良知说则似乎与主流的理学有所不同,良知的特点在于心和理的统一,既不是纯粹的普遍之理,也不是单纯的个体之心。在良知之中,情感、理性都兼而有之:个体之情和普遍天理在良知中融为一体。这里多少表现出一种沟通两者的尝试。
刘:杨老师,在良知这个概念里面,普遍性与个体性是统一面向的。在跨文化的背景下面,不同的文化对良知有不同的感受。就像一开始您所讲的实践把普遍性落实到具体情境中。普遍化原则加入跨文化语境里后,这样一种共识和普遍性或者良知,如何达成?
杨:良知常被译为“Innate Knowledge”或“Conscience”,但其独特内涵还需要关注。纯粹的“情感”不构成良知,纯粹的理性也不是良知,前者缺乏理性引导,后者则少了情感认同。从具体哲学家来说,可能有的侧重于理性这一面,有的侧重于情感这一面。程朱一系,比较侧重于理与普遍性这一面;陆九渊对个体性与情感性则给予较多关注。尽管不同哲学家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在他们的思想中,事实上理与情兼而有之,这一点在中西哲学家那里是有共通之处。不能说中国哲学都只讲“情”或仅谈“理”,如前所述,同一个哲学家,如孟子,既讲“恻隐之心”,也讲“心之官则思”,朱熹也是如此。现代西方的后果论,同样既注重情,又关注理性层面的计算。
刘:不论是实践,还是情理结构,都不可能用来标识中国伦理学的特点。是不是这样一种努力的方向就不对呢?也就是说,不要试图找到一个可以把中国区别于西方特质的笼而统之表述出来的概念。
杨:也许,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普遍的概念,但我还是比较认同先做具体的个案研究,在个案研究基础之上,再做一提炼。现在匆匆忙忙地用一个概念去概括中西的特点,难免以偏概全。经过个案的研究之后,不同特点可能会有所显示,由此再做一个总结,也许会更可靠一些。当然,在哲学和伦理学领域,人们总是需要用一些普遍概念,如感情、理性,不论中西方,都会用到这些概念。从这一角度来说,作为智慧的哲学,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但不同的哲学传统又都有不同的系统,用一般的概念去概括或描述,难免会发生各种问题。
付: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伦理知识,另一个是伦理学知识。在中国哲学中,大量讨论的是伦理知识;但我们要从伦理学知识建构的系统化角度来看,确实需要找到一些能够沟通中西的普遍性概念。
杨:从一些概念的区分来看,我们可以注意到中西思想的差异。中国人以人作为考察对象,思考如何成为人、怎样成事,都希望成就理想人格,成就人自身。就如何成己而言,从早期儒学开始,便涉及习和性的关系。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认为人具有普遍的潜能,但不同的“习”则使人彼此分离。后来,孟荀又分别发展出了不同的方面:孟子将“性相近”引申为性本善,突出了成己需要以善端为内在根据;荀子则侧重于人性中负面的潜能,肯定了后天化性起伪的必要。到了宋明时期,讲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实际上试图对孟荀加以折中。天地之性是完美的,气质之性则相当于荀子所讲的本恶之性,于是有了变化气质的要求,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习”的工夫。到了后来,进一步引向本体与工夫的关系,本体与性一致,工夫则属于习。王阳明提出“致良知”,其中“良知”是本体,“致”则是工夫。在中国哲学中,性、习、本体、工夫呈现彼此互动的关系,自我则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就。总体上,性习相统一是中国哲学的传统,本体—工夫的一致,以及致良知,都是由此衍化而来,其中的核心,则是围绕着“如何成就人自身”的问题。
刘:习与性成。工夫在变,本体在工夫中也会变。
杨:本体是发展的,工夫也在变化。黄宗羲讲“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已不同于预设一个先天本体,而是明确肯定,本体也是在工夫过程中形成的。这种理解已扬弃了传统儒学的看法:在孔子、孟子那里,性作为本体,主要是一种先天预设,但黄宗羲则在实质上将性(本体)看作是实践过程中生成的。这也可以视为中国哲学中观念的一种转换。
刘:那么,就实践智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而言:一方面,普遍原理如何落实到具体情境;另一方面,是不是也有倒过来的一个问题,普遍原则在具体情境中也要发生一些改变?
杨:当然,那肯定是要改变的,一般原则不能照顾到方方面面的,中国人讲经权,其中便包含变通的要求,原则如不变通,就容易变成独断僵化的教条。这也是中国以往思想希望避免的,变通是中国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伦理学的书写方式
付:中国伦理学贡献了大量的思想素材,尚缺少一个系统化的理论论证,要构建一种学术形态的伦理学恐怕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杨:确实,不管是在伦理学还是在认识论中,中国哲学都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体系。事实上,类似情况也存在于西方哲学中,其相关论说从早期来看也很难说已形成了现代视域中的体系,即使是《尼各马可伦理学》,也不同于纯粹的伦理学体系,其中很多方面缺乏严密论证。形成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伦理学系统,确是必要的。我在前述伦理学著作中,也尝试从一个方面来做这一工作。关于伦理学主要关乎什么这一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我将“善何以可能”作为一个核心的问题,由此来展开阐释。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其他方面来进行讨论。要对中国伦理学做形式化的整理,前提是对先秦,以及两汉、魏晋、隋唐、宋明时期的相关讨论加以反思、梳理、总结,看看其关心什么问题、如何展开讨论。从最基本伦理概念来说,当然离不开仁、义、礼、智、信,以及基本的伦理关系,如理欲关系、为己成己,等等,需要对此做具体的分析。但是,如果仅仅偏重于考察历史上这样一些伦理观念和术语,那就只是对已有的系统加以归纳整理而已。要形成能够回应西方伦理学概念的当代知识体系,仅仅做上述工作显然是不够的。这里需要“范围而进退之”。一方面,以中国伦理学为对象,自然应对传统加以关注,所建构起来的系统应体现中国的传统特点;另一方面,对西方哲学包括西方伦理学的讨论,也不能完全无视。总之,仅仅着眼于自身传统意义上的儒学或中国哲学来建构伦理系统,可能意义不大。在伦理学上,不仅需要关注中国的传统,而且应当对西方哲学有所回应;也就是说,应站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对东西方思想都有所消化和吸取。总之,不能仅仅限定于单一的传统:在单一的传统之下,不太可能做出为世界哲学或世界伦理学所接受的伦理系统。在这方面,现代西方哲学家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他们试图建构自身的系统,但又单纯关注自身的知识传统,未能充分考察西方之外的哲学传统,这带有明显的思想限定。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一方面要立足于中国已有的根基,另一方面又应面向世界,以兼容而非排斥的立场对待不同的哲学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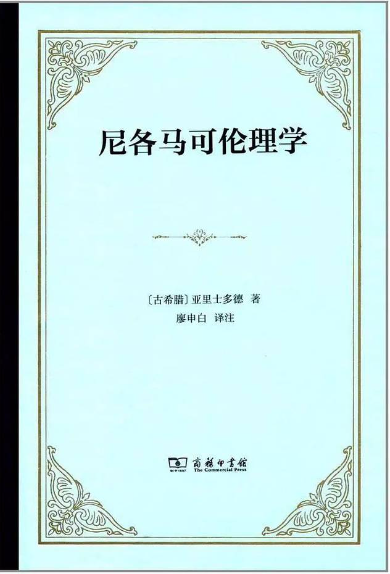
《尼各马可伦理学》
(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付:我在给学生讲《中国伦理学史》这门课时,就一直在想:怎么能做到,既不讲成中国伦理思想史,也不把它讲成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分。如何讲清楚中国伦理学的问题脉络,而不是思想的原生态。
杨:这里确实存在问题。思想脉络的把握是比较困难,在这一过程中容易分不清、理还乱。但是,从伦理学的观念出发梳理出一条线索,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作为一个研究者,本身需要先对伦理学概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然后根据这一认识,处理相关的论述。如果缺乏对伦理概念和理论的清晰认识,那可能就只能罗列伦理思想史中的不同材料。康德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等著作中,首先以自己的理解为讨论相关问题的前提。同样,在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时,也需要对一般伦理学层面的理论有所理解与概括,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概括梳理相关材料,并进一步反观中国伦理学的衍化。这里有一个不断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形成和深化相关的理论观念、把握伦理学的基本架构;另一方面,对中国伦理学的不同系统有所了解和认识,在伦理思想的梳理过程中印证相关理解。如果缺乏深入的理论观念,对中西伦理思想就可能难以梳理清楚。当然,思想构架本身并非是不变的,需要根据实际的材料不断地有所调整。这一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做伦理学历史的过程。对于伦理学的问题,在历史上有不同的看法。苏格拉底认为,伦理学涉及对“人应该怎样生活”的理解,中国人则注重成己与成物,为己指向的是如何成就自己,这也是对伦理道德的一种理解。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等著作中提出“道德行为如何可能”的问题,肯定只有通过善良意志来颁布各种律令,并按照律令去做而不考虑后果如何,才能有完善的道德行为,其中包含对伦理实践的看法。黑格尔则要回到伦理现实,走向市民社会、伦理、家庭、国家等,这也是一种伦理观念。关于伦理学是什么,不是只有一家之言,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理解,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便可立一说。伦理学的特点之一,是拒绝独断的教条,不是说只有某个说法正确。在一定的意义上,伦理学就是提供一种生活的解释模式。
刘:《善的历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一部儒家伦理学史。这本书在处理历史和逻辑的关系方面,堪称典范。比如:每个人物有几个关键的命题,同样一个命题在不同哲学家那里又展现为历史的衍化。
杨:确实是这样,做一个笼而统之的概括,常会遇到困难。三十多年前,我写这一著作的时候,也曾走了一些弯路。我本来想以问题为主线,但论述过程每每面临重复的问题,如义利之辨作为一个问题,尽管在每一个时期都有差异,但仅仅以此为主线,也会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所以,我最后还是取消了原定计划,改为以历史人物和问题相结合的方式来展开,因为这样更容易把握。
刘:有些问题您处理起来,可能在某一章就略一些,甚至就不讨论。
杨:对,如果单以问题为主线就会容易造成一些重复,两相结合着做,就可以避免一些重复。
刘:当时,这个构思也是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调整过程吧?
杨:是的,当时按照问题线索来写,已经完成好几万字了,后来觉得不行,又回过头来重新做。研究过程总是需要面对现实,不断调整,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否则,结果就很难让人满意。回到伦理思想研究的问题:要概括中国伦理学思想,首先需要有一个理论上的构架,否则便会面临剪不断、理还乱的状况。构架很重要,概括伦理学史的演化历史,需要根据思想的实际情况梳理脉络,在面对大量伦理学史材料的时候,原来的设想可能需要面临调整,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不管处理什么样的历史问题,理论构架、理论准备不可或缺。一下子陷入思想史资料里后,就容易摸不着边,找不到北:这么多的材料,每个人的情况似乎大同小异,不容易刻画和把握。但细究起来,不同哲学家对伦理问题的理解、所运用的伦理学的概念系统,实际上存在各种差异。我们需要先冷静思考,结合已把握的伦理学理论和伦理学的概念系统,在纷繁复杂的思想材料中梳理出一条线。作为一种解释系统,这种梳理可能只是一家之言,但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够对历史与现实给出合理的说法,便可成立了。这里无须追求定于一尊,也不必执着所谓“原义”:按照解释学的观点,回到原义是不太可能的。
刘:正如《伦理与存在》也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这个概念框架和《善的历程》可能是不一样的。如果从《伦理与存在》这个概念框架来反观中国伦理学,可能又要有一个新的伦理学史的写法。

《善的历程》 杨国荣/著
(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杨:我在该书中将“伦理”与“存在”,也就是伦理学和人的存在放在一起,从另一个角度说,其中体现了对本体论问题和伦理学问题相关性的肯定。这一思路也具有“个性化”特点。引申而言,“具体形上学”的提法也是以前没有的。哲学需要创造概念,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曾有类似的看法。当然,这种构造需要有根据。我刚刚讲的意思是,或许不一定每一位研究者都需要建构系统的伦理学原理,同时,对中国伦理学史也可以有不同的概括。本体论与伦理学思想的统一,这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视野,在伦理学上,还需要追问具体的、合乎中国伦理学史的问题。中国哲学以“何谓人”“如何成就人”为关心的具体问题,为己之学即以如何成就人为核心的关切。从“人禽之辨”(什么是人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到如何成就真正意义上的人,体现了理论的进展。人非现成的,唯有通过后天的成就过程,才能达到人的理想形态,所谓“成性”或“成己”便体现了后一意向。此外,儒学所说的“为己”以自我成就为理想的目标,这可以成为人的道德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总之,何谓人,如何成就人,这是中国哲学关心的问题之一,其他问题往往与之相关。
刘:杨老师的《伦理生活与道德实践》这篇论文从“活着”的角度提供了一个框架:为什么活着?如何活着?如何活得好?活得怎么样?
杨:所以,我和李泽厚的看法不同,李泽厚把“为何活”放到了最后。实际上,“为何活”或“为什么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具有前提性意义的追问。中国人讲“为己”,便与人的存在价值相关,各种选择都以此为依据。“如何去活”以“为何而活”为前提:只有确立了价值目的,才能选择与之相关的“活法”;以某种目的为价值方向(“为何活”),则需要以相关的方式为生活途径(“如何活”)。
刘:这样的框架很朴实,很多根本问题已经包含其中。康德提出的四个问题看起来也非常简单:人是什么?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
杨:在理论上总是需要面对现实,否则容易华而不实。
付:我们现在对伦理要有一个广义的理解,要回到生活世界和伦理实践上。
刘:杨老师,您如何看待普遍价值与共同价值的关系?
杨:伦理学本身是普遍性的东西,并非仅仅对某一个特定群体有意义。不过,这里所谓普遍性,离不开某种传统,也更需要基于现实。康德非常注重人是目的、普遍性原则,这也构成了其伦理学的特点。伦理学确有一些普遍性的东西,伦理学的目标本身也是要建立一种普遍性的道德秩序。当然,康德可能过于强调道德形式之维,事实上,道德还有其现实性的一面。人类为了能够和谐生存,需要建立一种共同的道德秩序,以此来为人的存在提供条件,后者涉及道德的现实性,道德作为保证人类和谐共存的条件之一,即体现了这种现实性。康德完全忽略道德行为的结果,同时也未能对道德的现实性这一面向给予必要关注。事实上,道德既有崇高性的一面,也有现实性的一面,康德只讲崇高性,不讲现实性,不免过于抽象。
刘:康德强调形式化、普遍化。这里的难题是,对于道德原则来说,我们能不能有一种超越时空意义上的普遍性?
杨:在我看来,道德既有普遍性的一面,又有历史性的一面。从最一般原则来说,它并非仅仅适用于一时一地,而是具有超越特定时间与空间的性质,但同时,道德在不同时代又有不同特点,前现代的道德观念和现代意义上的道德观念便并不一样。传统的中国伦理观念包括天—地—君—亲—师,现在“君”已不存在,只能说天—地—国—亲—师,这里便包含思想的历史转换。从以上方面看,中国伦理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天—地—君—亲—师体现的是前现代的要求,天—地—国—亲—师则代表了当下的要求。道德的普遍性和历史性不能偏废:仅仅承认其中之一,可能悖离历史实际。

天地君亲师位
(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付:在道德的普遍性和历史性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反思德性与规范的关联与张力。
杨:在中国传统历史上的仁、义、礼、智、信等观念中,仁指内在的德性,礼表现为外在的规范,义则是“应当”与具体情境中适宜的统一,智则表明。以上各个环节包含理性的意识与理性的指导:道德本身具有自觉的性质,理性则是自觉性的保证,信包含诚信、信誉。关于特定规范,历史上有不同的概括,亚里士多德讲的中道、勇敢等品格和德性,孔子所说的仁、智、勇,都可以视为这一类的表述。讲中国伦理学,自然需要关注中国已有的各种传统思想对伦理规范的理解,由此进行概括。传统伦理中,仁、义、礼、智、信可能体现了综合性;比较而言,在理学的理欲之辨中,程朱一系在突出天理、贬抑人欲的同时,又进一步把“道心”视为主宰,则多少包含某种片面性。德性与规范的相互关系是具有普遍性的伦理问题,这一问题并不是中国哲学所特有的。我在《伦理与存在》中专门有一章讨论德性伦理及其内涵。当然,不排斥从德性与规范的关系这一角度来梳理中国伦理思想,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问题并不只存在于中国伦理学中。关于两者如何沟通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总体上,德性与规范在中国哲学中并非泾渭分明、相互对峙,而是都得到了某种关注,可以说是兼而有之。就其起源而言,规范在中国哲学中常常被视为德性的提升和普遍化。郭沫若在谈到礼与德的关系时,已注意到这一点:“礼是由德的客观方面的节文所蜕化下来的,古代有德者的一切正当行为的方式汇集下来便成为后代的礼。”这里的“礼”主要表现为一种规范系统,“德”则与现代所说的德性相关。依此,则历史上的“有德者”或圣人的德性在形式化、普遍化之后,便衍化为规范系统(礼)。中国伦理学中固然有很多关于规范伦理学或德性伦理学的内容,但兼顾德性与规范,可能更多地突出了中国哲学的特点,在宋明理学中,这一特点也非常明显。
付:对于如何构建中国伦理学的当代形态,理论与方法都是至关重要的。
杨:是的,但需要基于思想史或伦理学史来讲方法的问题,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也体现了这一原则。
付:非常感谢杨老师拨冗指导,真是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