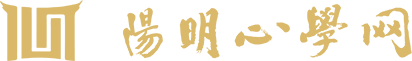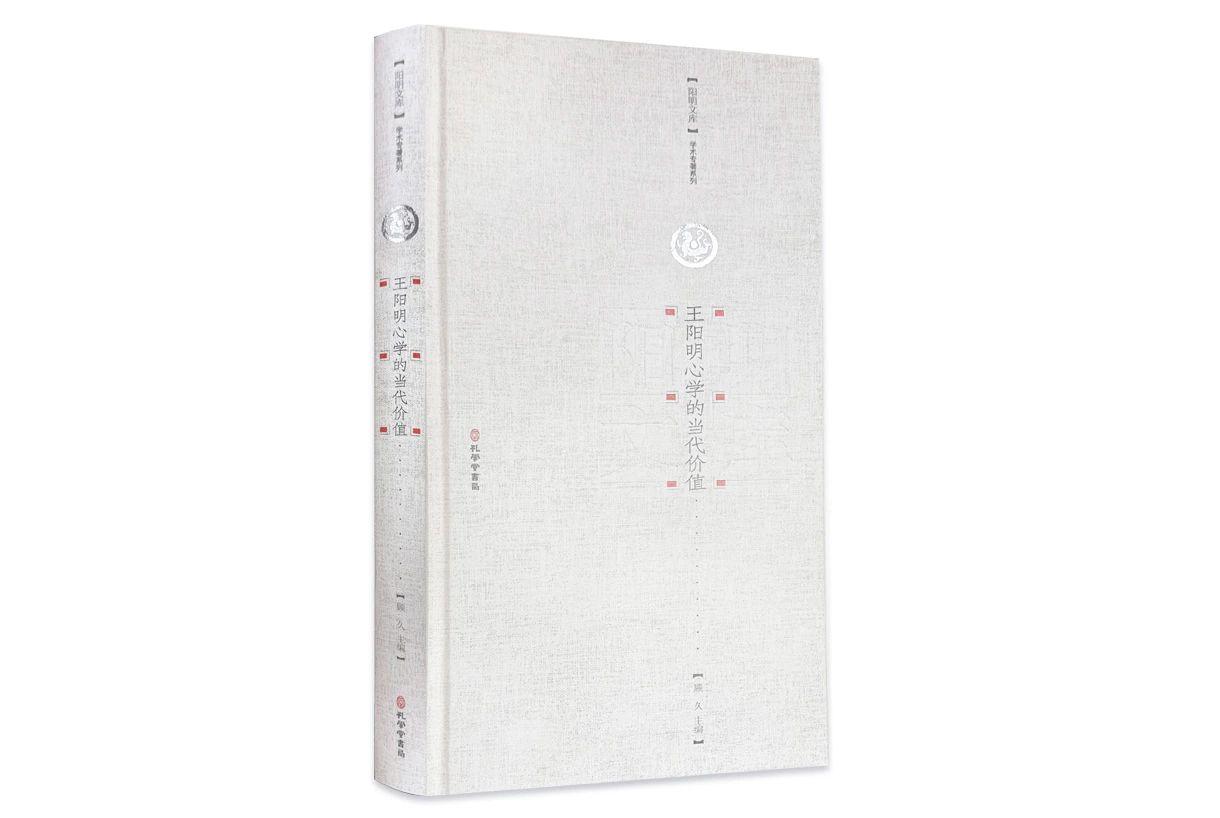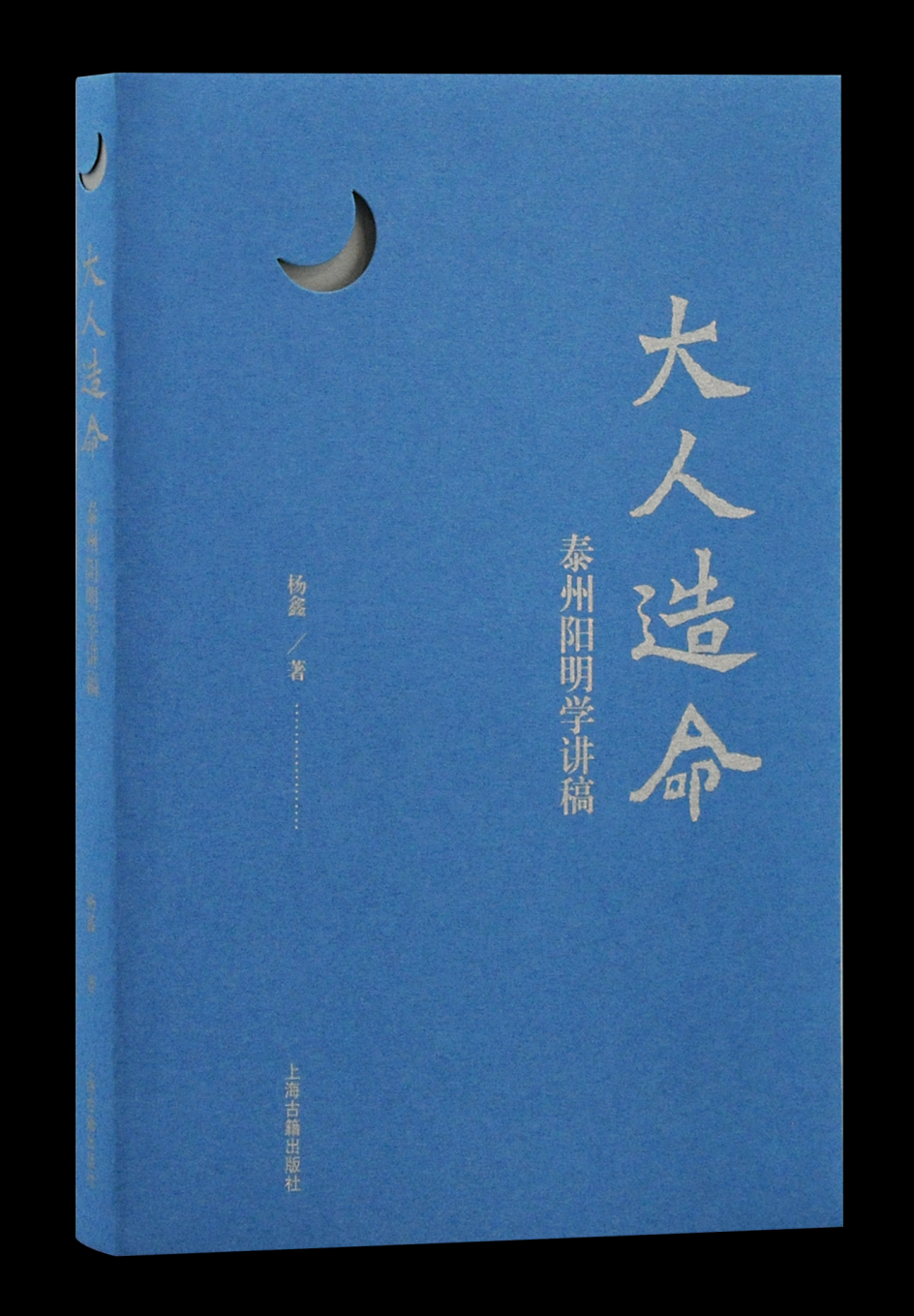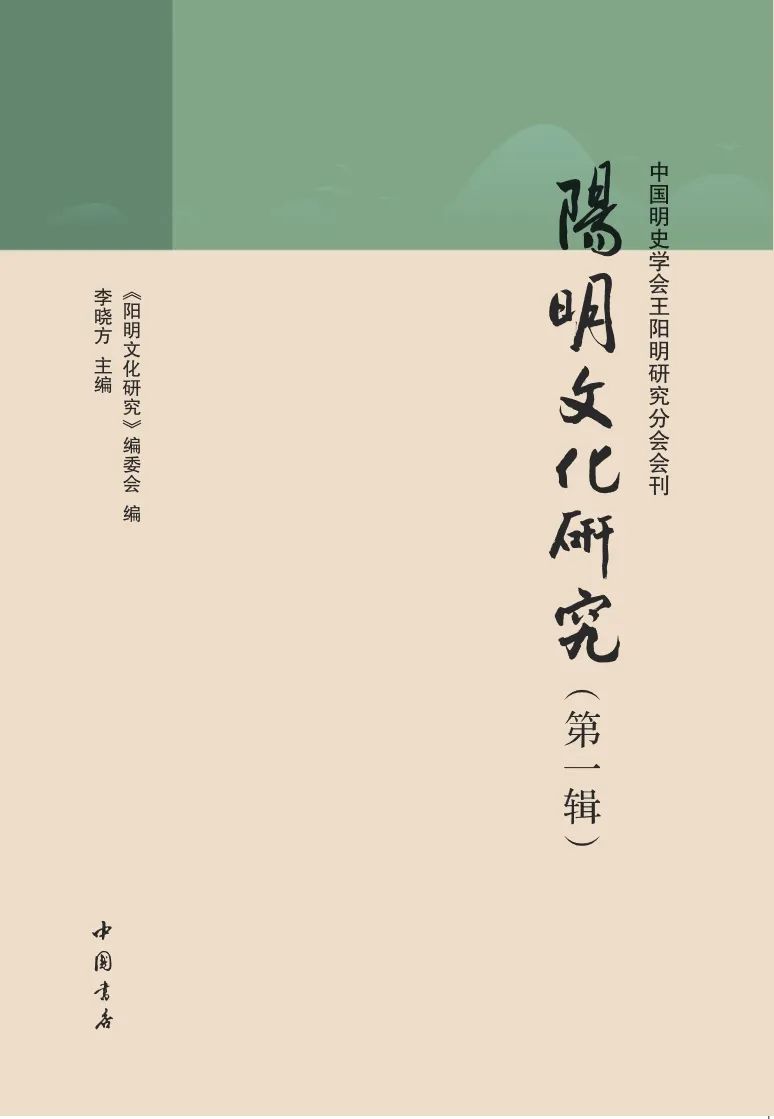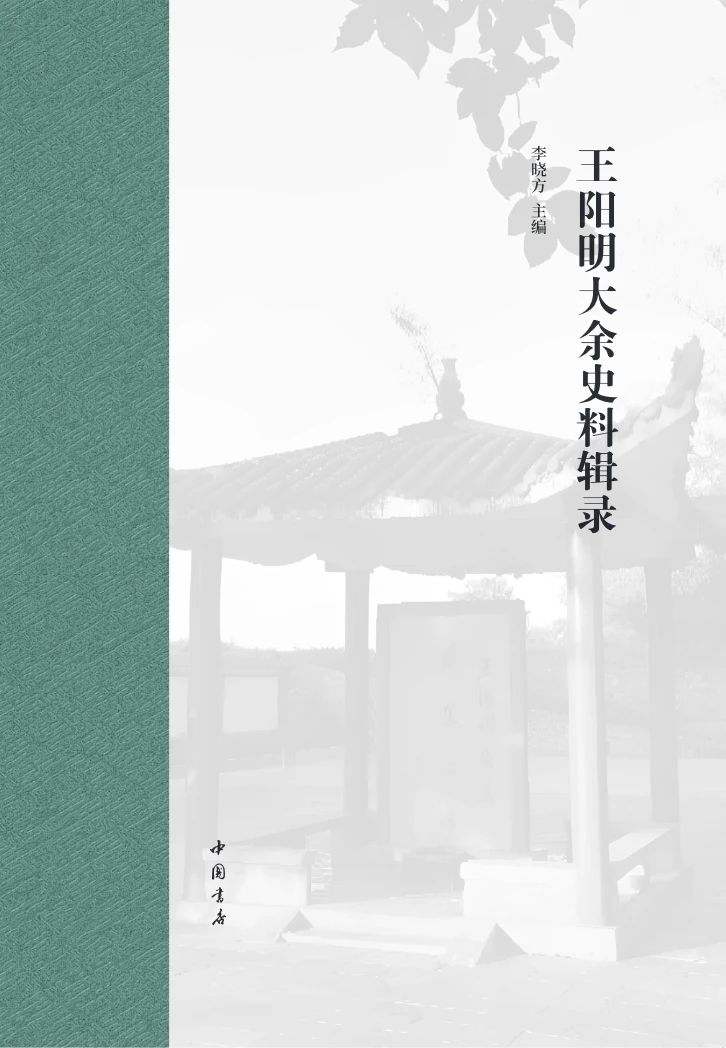《以人观之:走向人性化的存在》
推进世界走向合乎人性的形态。

书 名:以人观之:走向人性化的存在
丛书名:哲学与生活世界
作 者:杨国荣 著
ISBN :978-7-108-08143-8
定 价:89.00 元
页 数:336页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编辑推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具有“人的一般本性”, 这种本性便可以视为人的普遍本质。马克思要求使劳动过程适合“人类本性”,意味着扬弃劳动分异化,它构成了走向合乎人性即人的理想存在形态的前提。本书的出版,将深化对人性及合乎人性的理解。有助于使人们关注人的存在意义,通过自身的合理、正当行为,以推进世界走向合乎人性的形态。
内容简介
人既存在于历史过程,又是历史的主体;理解历史的演进与人的存在,离不开对人及其存在方式的考察。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以道观之”,侧重于从形而上的层面理解世界;与之相关的“以事观之”,则主要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沟通中把握存在。然而,不管是“以道观之”,还是“以事观之”,归根到底仍是“以人观之”:“以道观之”和“以事观之”的主体都是人,从而从实质的层面看,最终乃是人“以道观之”,或人“以事观之”。这种“观”,也就是从人的视域出发,考察世界之在与人的存在。 “以人观之”的“观”,并非“旁观”或“静观”:它乃是在作用于世界中考察或把握世界本身。在参与现实世界的生成过程中所形成的“观”与人所作之“事”的展开呈现一致性。所以本书也可以看作作者此前在具体形上学之域所作思考的延续,就其内容而言,是《人与世界:以事观之》的姐妹篇。
本书指出,合乎人性的历史发展,表现为一个过程。一方面,人是目的,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人的自由趋向同样构成了人的本质特征,人的发展需要合乎以上内容;另一方面,如前所言,这种规定又与人性自身的不断深化相关。从人的自由看,在人的内在感性取向处于主导地位时,人格自由便难以达到;当人对必然性还缺乏把握、外部必然尚支配人的行为时,合乎法则意义上的自由也无法企及。通过克服物种限制、超越内在感性与外在必然的限定而提升人的自由之境,是人性化涉及的实质向度。随着人性与人性化内涵的历史变迁,人的衍化过程将不断扬弃非人化而走向人性化,这一历史过程所趋向的理想目标,则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作者简介
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院长,西北师范大学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第六届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学术兼职包括国际形而上学学会(ISM)主席、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国际中国哲学学会(ISCP)前会长(2019—2022)、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等。
实拍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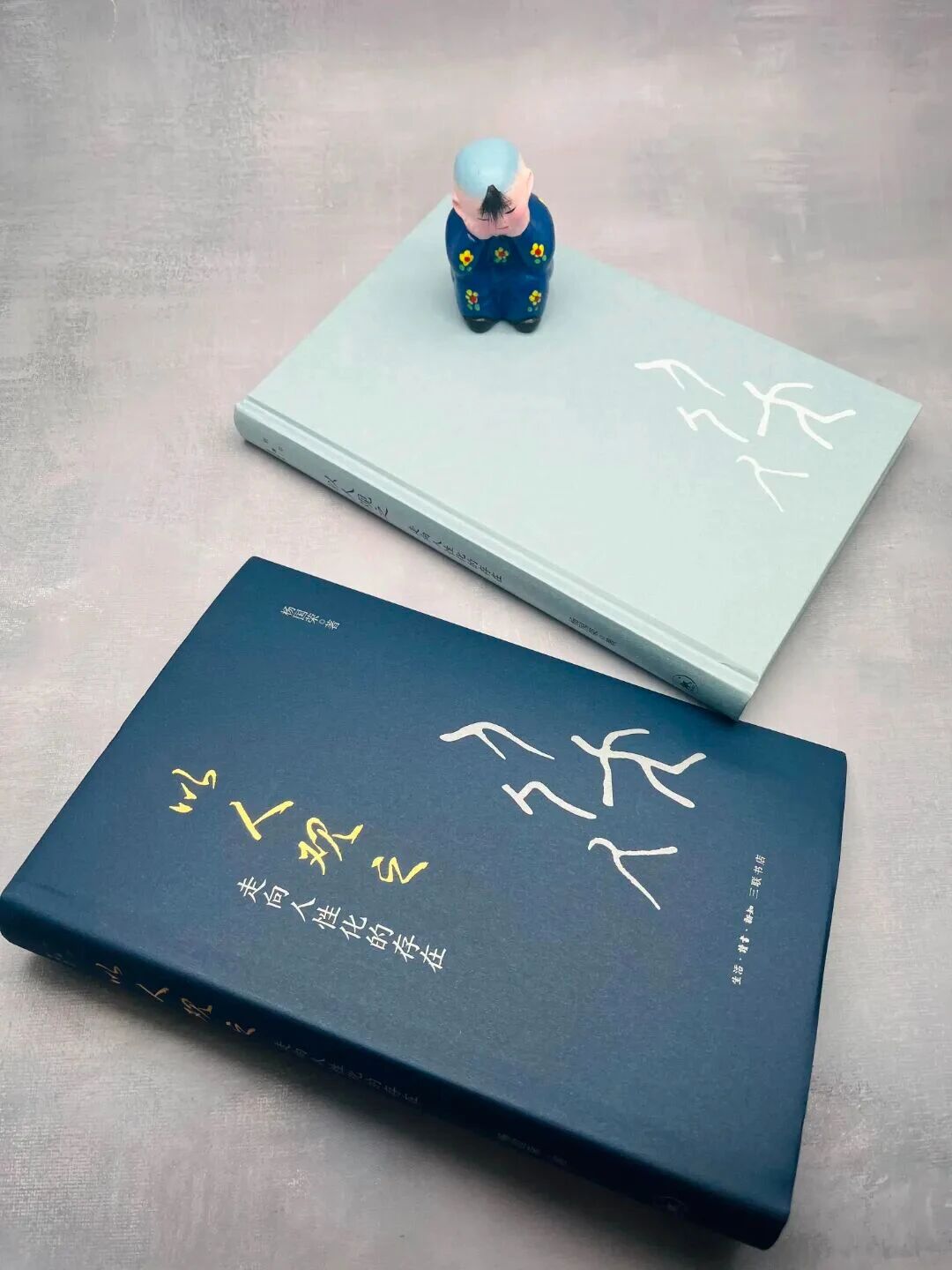
全书目录
导 论 /
一 现实存在与人化之“在” /
1. 两重世界 /
2. 以事成之 /
3. 人化存在及其不同维度 /
二 人类认识的多重含义 /
1. 知识的实质内涵 /
2. 多重形态 /
3. 知与所知 /
4. 知识的生成与衍化 /
三 存在的价值之维 /
1. 道德与伦理 /
2. 终极关怀与精神追求 /
3. 社会有序与政治正当 /
四 世界的意义 /
1. 意义与人 /
2. 不同的面向 /
3. 目的之维及其他 /
五 天人之辩的内蕴 /
1. “天之天”与“人之天” /
2. 文野之别:天人之辩的展开 /
3. 天的超验化及其含义 /
4. 天性与人性 /
六 “活着”与人的生存 /
1. 人“在”世的前提 /
2. 生存的多样之域 /
3. 生命的限度与创造活动的恒久趋向 /
七 如何生活:存在过程的展开 /
1. 人的生活与人的存在 /
2. 生活的双重形态及其意义 /
3. 生活的完整性与人的完整性 /
八 生活的伦理之维 /
1. 伦理生活的多重内涵 /
2. 人的存在及其感受 /
3. 伦理生活与道德实践 /
九 走向人性化的存在 /
1. 人性的不同向度 /
2. 历史性与过程性 /
3. 人性化何以可能 /
附 论 /
中国哲学中的人性问题 /
附 录 /
哲学之思:视域与进路——杨国荣教授访谈 /
后 记 /
索 引 /
精彩选读

中国哲学中的人性问题
一
人性的讨论首先涉及广义之“性”及其内涵。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性”这一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与现代哲学中的“本质”范畴处于同一序列。孟子已比较早地对性做了考察,其基本的看法是“天下之论性也,则故而已矣”。依此,则关于“性”的讨论,实质上展开于“故”这一层面。如所周知,“故”包含事物的根据、原因等义,从而与今天所说的“本质”概念有相通之处。在西方哲学的语境中,与“性”具有较为直接的对应性的概念主要是nature,后者也内含“本质”的之义。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诚然需要注意“性”与“本质”的不同侧重点,但同时亦应关注两者的相通性,不能否认和忽视这两者作为哲学概念所涉及的相关问题。
与以上问题相涉的是“人性”与“人的本质”之间的关系。在具体的应用以及哲学讨论中,两者有时呈现不同的侧重。在某些场合,“人性”的概念与“本性”的概念相通,从而更多地与既成、已然的形态相联系,表现为人本来具有、无法分离的规定。谈到某物的本性,通常便是指该事物一旦存在便与它同在这种内在规定,人的“本性”也常被赋予类似的含义。相对而言,人的本质这一概念则侧重于更深层的社会意义:当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时,便表现为在上述意义上具体运用这一概念。人的这种本质,并非与生俱来。人最初只是生物学上的存在,人之获得以上本质基于广义的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过程,人的本质本身也逐渐地形成于这一过程,从而带有生成的意义。存在主义有如下名言,即存在先于本质。这一看法包含解构本质主义的意向,其逻辑的含义之一是人的本质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人首先是被抛掷到这个世界,然后通过自己的筹划、选择等过程,逐渐形成自己的本质。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也赋予人的本质以生成性。可以看到,人性和人的本质在具体运用中存在如下差异:比较而言,人性更多指已然性、既成性,作为既定形态,它无法被选择;本质则更多地与生成过程相联系。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正如前面提到的“性”和“本质”并非截然相分一样,“人性”和“人的本质”这两个概念也有相通之处。关于人性,无论是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中,还是在西方哲学的意义上,都不仅指一般意义上的本性,而是同时表示人不同于其他存在的根本之点。从中国哲学的角度来说,人性侧重的是人不同于“鸟兽”或“禽兽”之性:中国哲学讲人性,往往和人禽之辨联系在一起,这一意义上的人性所表示的同时也是人不同于禽兽的根本特点。在西方哲学中,关于人性的理解也有类似的含义。休谟著有《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从题目上看,这部著作讨论的就是人性问题;就具体内容而言,它既谈到“人的理解”(human understanding),也谈到与道德相关的情感问题(passion、sympathy等)。无论是广义上的“理解”,还是道德意义上的情感,都是人区别于一般动物或其他存在的规定之一。就此而言,休谟论人性,实际上也侧重于人不同于其他存在之点。杜威在20世纪曾出版《人性与行为》(Human Nature and Conduct)一书,其中亦以人性为重要论题,并将人性与人的行为联系起来,强调对行为规则的遵循、理想的实现,都要以人性的内在自觉为前提。晚近一些哲学论说,也有类似趋向。如在《牛津哲学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中,便有一个“人性”(human nature)的条目,其解释则与人的本质(“what it is essentially to be a human”)相联系。可以看到,无论从中国哲学的历史来看,抑或就西方哲学的背景而言,谈论人性问题都涉及人不同于其他存在的根本之点。从而这一意义上的“人性”概念与“人的本质”概念也存在相通之处:宽泛而言,人性或人的本质,都关乎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特征和内在规定。
进而言之,我们还需要区分“人的本质”或“人性”与“人的真实存在”或“人的具体存在”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如前所述,人的本质是人区别于其他存在(包括动物)的根本之点,但是,人的真实存在或人的具体存在却不仅包含其本质,而且还涉及人作为动物或生物所具有的各种规定性。作为真实而具体的存在,人并不是以赤裸裸的本质形态出现的,他同时还包含更广意义上的动物性、生物性。马克思曾指出:
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马克思首先肯定吃、喝、性行为等等机能是“真正的人”所具有的,也就是说,他是以真实的人(“真正的人”)作为理解人的背景。然而同时,马克思又强调,以上机能如果离开了人的其他社会活动,仅仅以抽象的形式存在,便只是一种动物的机能。在这里,他既把动物的机能与真正的人联系起来,又将单纯的动物机能与人区分开来。所谓“真正的人”,也可以视为具体的、现实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现实的人来说,动物机能当然不能加以忽略:如果无视这些机能,人便只能呈现为一种抽象的、光脱脱的本质,而不再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具体存在。这样,谈到真正的人,便需要同时关注其动物性的方面,这些方面从哲学的意义上说,也就是人的存在中属感性之维的规定。然而,如果要将人跟其他存在(包括动物)区分开来,便必须联系人的本质,关注人性。在这一意义上,把吃、喝、性行为等理解为“真正的人”的机能之一与肯定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不是完全不相关或相互对立的。可以说,前者是在把人理解为具体、真实的存在这一意义上说的,后者则突出人之为人的本质。在理解人的时候,这两个方面(一是人的本质,一是人的感性规定)都需要注意。在把人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时候,关注的主要是人不同于其他存在的根本之点(人的本质);在把握人的真实、具体存在时,则需要同时考察人的多方面规定。要而言之,人性问题、人的本质问题与人的真实存在、具体存在应当联系起来考察,对人的理解既不能限于自然的机能,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本质层面之上。
二
以下的讨论回到中国哲学关于人性问题的理解之上。在中国哲学中,对于人性的理解并不是仅仅就人性而谈人性。前面已论及,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关于人性的讨论,涉及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何为人”或“人是什么”。中国哲学(包括儒家哲学)当然没有以现代的形式明确地提出以上问题,但是从其实际的注重之点来看,它在理论上关切的实质上就是何为人的问题,这一点从儒家的人禽之辨中便不难看到。如前所述,儒家讨论人性问题,与人禽之辨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试图通过对人性的理解和规定,将人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在儒家的性善说中,人性本善的理解便与“何为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如所周知,孟子曾提出四心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稍做分析便可知,“四心”在广义上都涉及道德意识,其中又有不同的侧重: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在宽泛的意义上可以理解为道德情感,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则更多关乎自觉的理性意识。对孟子来说,只有具备了这些基本的道德意识和理性意识,才可以称之为人。孟子还特别提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是非常关键的概念,并不是说人与动物没有什么差别,恰恰相反,它体现的是人禽之别的根本之处。按朱熹的说法,“虽曰少异,然人物之所以分,实在于此”。这些根本之点,就是前面提到的四端,特别是其中所隐含的道德意识及理性意识。在孟子看来,正是这些基本之点,把人和其他存在区分开来。可以看到,孟子对人性的理解,与他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理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里还需要讨论一个问题。从外在的方面看,孟子对人性的理解似乎存在一种“张力”。一方面,孟子肯定人皆有“四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另一方面,又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以上两者似乎相互背反: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等人皆有之,意味着凡是人都有恻隐之心等;而“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则在逻辑上预设了可能存在人缺乏恻隐之心等情况。这里的关键在于本然和当然的区分。根据孟子的理解,从本然的层面说,人生来都具有四心(道德意识及理性意识),但是从现实存在形态来看,由于各种原因,人所具有的各种道德意识可能会失落,而一旦失去了这些规定,则人便不再成其为本来意义上的人。正是基于后一事实,孟子指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其放心的前提是心虽然本来具有,但后来失落了,德性修养的作用之一则在于将这种本来具有后来失落的东西再找回来。如果说,人皆有四心属本然,那么,“求其放心”的过程便属于当然。从以上方面看,前面提到的孟子的那双重看法之间,便并非彼此矛盾:从本然的形态来说,人皆有恻隐、羞恶等道德意识,但是在现实的存在过程中,这种意识有可能会失落,四心一旦完全失落,人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了。孟子之所以特别强调“求其放心”,就在于让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会批评那些完全违背道德原则、做伤天害理之事的人,甚至对其愤而怒斥:“简直不是人!”这种批评也是从当然的层面做出的。
可以注意到,对孟子而言,本然既与现实形态合一,也与当然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从出发点来看,人本然地就具有道德意识和理性意识,从而在本然意义上都是人。现实形态则有其复杂性:作为人性的规定,两者具有合一性质,善端与现实人性也无根本区别;就现实社会或现实存在而言,则又与最初的人性合一呈现不同特点。在现实存在过程中,那些已有的道德意识可能会失落,所以还需要成其“当然”,所谓“求其放心”就可视为达到当然的具体途径。在孟子那里,达到当然同时意味着回到与现实一致的本然。
比较而言,在儒家的另一系统荀子的哲学那里,对人性则呈现另一种理解。荀子认为,人的天性属于“本始材朴”:“性者,本始材朴也。”这种天性既非善,也非恶,其特点在于自然而然,所谓“不事而自然谓之性”。然而,如果任其自发衍化,则可能趋向于恶:“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因此,需要通过“化性起伪”的过程,加以约束和引导:“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这里,人性被规定为本然与现实两个层面:在“本始材朴”的意义上,人性处于本然的阶段。其现实的形态则表现为两个层面:顺乎本然的自然之性(“顺是”),人性取得“恶”的品格,这种形态可看作一阶的现实人性;经过“化性起伪”而变革人性之“恶”,使之归于礼义(“伪起而生礼义”),由此形成的人性则可视为二阶的现实形态。可以注意到,荀子对人性的看法包含着对性的不同形态的区分:以“本始材朴”为形式,荀子肯定了人性的本然形式。与之相关的是现实的人性,后者又被规定为双重形态:以“顺是”为进路,人性表现出负面的趋向;在“化性起伪”的前提下,人性取得了与礼义一致的形式。在此,对应于“顺是”与“化性起伪”,人性的现实形态具有不同内容。质言之,人性中恶的趋向一方面不同于本然,而表现为现实的初始形态;另一方面又与“当然”难以相容。“当然”意味着合乎礼义规范,在荀子看来,从具有负面意义的人性到“当然”之性,需要经过“化性起伪”的过程。不难注意到,荀子对人性的理解与孟子的实质差异,在于更明确并自觉的区分人性的本然趋向与现实形态。
进一步看,按荀子的理解,只有通过“化性起伪”、改造趋向于“恶”的负面之性,才能获得具有正面真正意义(合乎礼义)的现实人性。这一点,从荀子有关人性的一些论述中可以较为清楚地了解。荀子在比较人与其他存在时,曾指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里所说的“知”包括知觉、欲望等,前面所引关于性恶的论述中,荀子已提及,人一开始便具有各种自然的欲望,如耳目、声色之欲等等,这些都属于广义上的“知”。在荀子看来,上述之“知”固然具有现实形态,但仅仅具这一意义上的“知”,并不表明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相反,唯有从这一层面的“知”进一步提升到“义”,才成其为他所确认的人。也就是说,人不同于其他存在的根本之处,在于“有义”。因此,具有负面形态的人性固然已通过“顺是”的活动而取得现实形态,但仍不同于具有正面意义(合乎礼义)的人性;只有通过“化性起伪”而达到包含“义”的人性,才趋向于真正意义上的人。在此,关于人性的讨论上,同样与“何为人”的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儒家之外的系统,如道家,在某种意义上把人的天性理解为真实的人性。初看,道家关于人性的讨论与“何为人”的问题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很紧密:把自然意义上的存在规定视为人性,意味着将人与自然沟通起来,而不是指向真正意义上的人。然而,如果做进一步分析,则可看到,道家哲学系统中所说的天性,已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自然之性,而是被赋予价值意义、被理想化了的规定。在道家看来,以礼义为内容的人性意味着对天性的扭曲、戕贼,与之相关的存在并不是人的本真形态。唯有剔除了人化的内容,回复本然的天性,才能达到人的真实存在。不难注意到,在实质的层面,道家对人性的理解,与“何为人”(什么是本真形态的人)这一问题也存在内在关联。就本然与当然的关系言,道家也表现出以本然为当然的趋向,在这方面,道家与孟子具有相近之处。不过,两者对本然的理解又存在实质的差异:在孟子那里,本然之性包含德性内涵(表现为仁、义、礼、智之端);道家则以自然之性(天性)为本然,并将这种自然的天性与人化意义上的世俗内容加以对立,主张“无以人灭天”,反对“失性于俗”。在这里,道家与儒家对人的不同理解,与他们对人性的不同看法具有理论上的相关性。这一事实从另一个方面表明,在中国哲学中,人性问题与“何为人”这一更根本的问题无法相分。
三
进而言之,“何为人”与“如何成就人”在逻辑上彼此联系。事实上,由以上所述做进一步考察便可以发现,人性的问题不仅涉及“何为人”,而且关乎“如何成就完美的人”“如何达到道德上的完善之境”,后者所讨论的也就是中国哲学所说的“成人”问题。考察中国哲学史上的人性问题,常常容易就人性理解人性,然而从内在的理论意蕴看,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在于把人性的讨论与追求更完善的人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质言之,人性的问题并非孤立存在,对人性的规定在本原的层面构成了“成人”理论的前提。
以儒家而言,人禽之辨与圣凡之别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如前文所一再论及,在儒家(如孟子)看来,人与禽兽的根本不同在于人具有恻隐之心等善端,这种善端既使人区别于动物,又为人走向完美的存在形态提供了可能。圣凡之别,则涉及是否能够将以上可能转化为现实:圣之为圣,就在于能够将善端扩而充之,使人不仅区别于禽兽,而且进一步把走向完美的潜能转化为现实的人格。唯有完成这种转换,才能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又达到理想的人格之境。这里可以更具体地注意到人性理论与成人学说之间的内在关联。
从以上前提考察孔子关于“性”的看法,便能获得比较具体的理解。如所周知,孔子论“性”,兼及“习”:“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宽泛而言,“习相远”中的“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习俗,即广义上的社会环境;一是习行,即个人的知行活动。在孔子看来,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尽管他没有明确指出相近之性究竟是善还是恶),然而由于后天环境、习行的不同,个人的人格便形成了差异。在孟子那里,“性相近”被引申为“性本善”。按孟子的理解,正是这种本善之性为人成就完美德性提供了可能,这种可能同时构成了人格完善的内在根据。这样,对孟子来说,完美的德性并不是外在的强加或灌输,而是以内在的可能性作为出发点。从理论上看,孟子强调性善说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从人性的层面,为成就完美的人格提供内在的根据和前提。人皆可以成尧舜,其前提就是人皆有作为成圣内在根据的本善之性。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解释,为什么中国哲学不需要超越的上帝或超验的存在作为超越有限的至上之源:在中国哲学特别是孟子一系的儒家哲学看来,人自身的本性中已经包含这样一种内在根据,个体只需要把这种根据加以扩充,就可以完善自己,达到人格上的完美。
与孟子有所不同,荀子着重发挥了孔子“习相远”之说。从逻辑上说,既然人性本恶,而本恶之心又不能成为走向完美人格的根据,那么,就需要通过后天的习俗(环境)与习行,“化性起伪”。荀子强调用后天的礼义,包括法律规范等等的引导、约束,来改变人的本恶之性,使人由此走向完美之境。在这里,荀子的人性理论也构成了其人格完善理论(成人学说)的前提:正由于人性一开始并不具有善的趋向,后天的化性起伪、礼义教化便必不可少。化性起伪、礼义教化的具体内容,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习”,包括习行与习俗。可以看到,孟、荀在不同的方向上展开了孔子对人性的理解,并且进一步把它和人格的完善联系在一起。两者尽管出发点不同,但追求的目标却是一致的:无论是孟子,抑或荀子,都既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也以此为成人的目标。当然,两者所确认的成人前提又存在差异:孟子强调人性本善,由此肯定人具有成就完美人格的内在根据,对孔子所说的“习相远”未能给予充分关注。荀子区分了人性的本然形态与现实形态,人格的完善不仅以本然到现实的衍化为指向,而且相应于现实人性的不同内涵,表现为通过化性起伪而由初始的(一阶的)现实人性向合乎礼义的(二阶的)的现实人性转化,所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便突出了后一趋向。对荀子而言,“本始材朴”的本然之性只是最初的对象和依托,无法成为人格涵养的现实出发点,达到“完美”人格之境主要依赖于后天的人为和努力:“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正是基于这一看法,荀子一再指出:“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化性起伪的具体内容,也就是通过社会的影响与个体自身的作用,以变革经过“顺是”的后天自发衍化而趋向于否定形态(恶)的现实人性,使之合乎礼义。这里,理想的人格一方面不同于“本始材朴”的本然之性,另一方面也有别于自发衍化而形成的否定形态的人性(以“恶”为呈现形态之性)。不过,荀子在肯定后天作用的同时,对成人的内在根据不免有所忽略,与之相应的是把人的成长看作外在灌输、强加的过程,所谓“长迁而不返其初”。后来秦代趋向“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强化外在社会规范的约束的作用,这与荀子的观念似乎也具有某种思想的联系。要而言之,从人性理论来看,孟子与荀子既各有所见,也各有所偏;而在对人性理论的不同阐发中,他们同时又展示了讨论人性问题的具体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