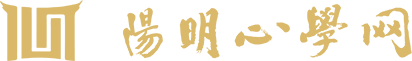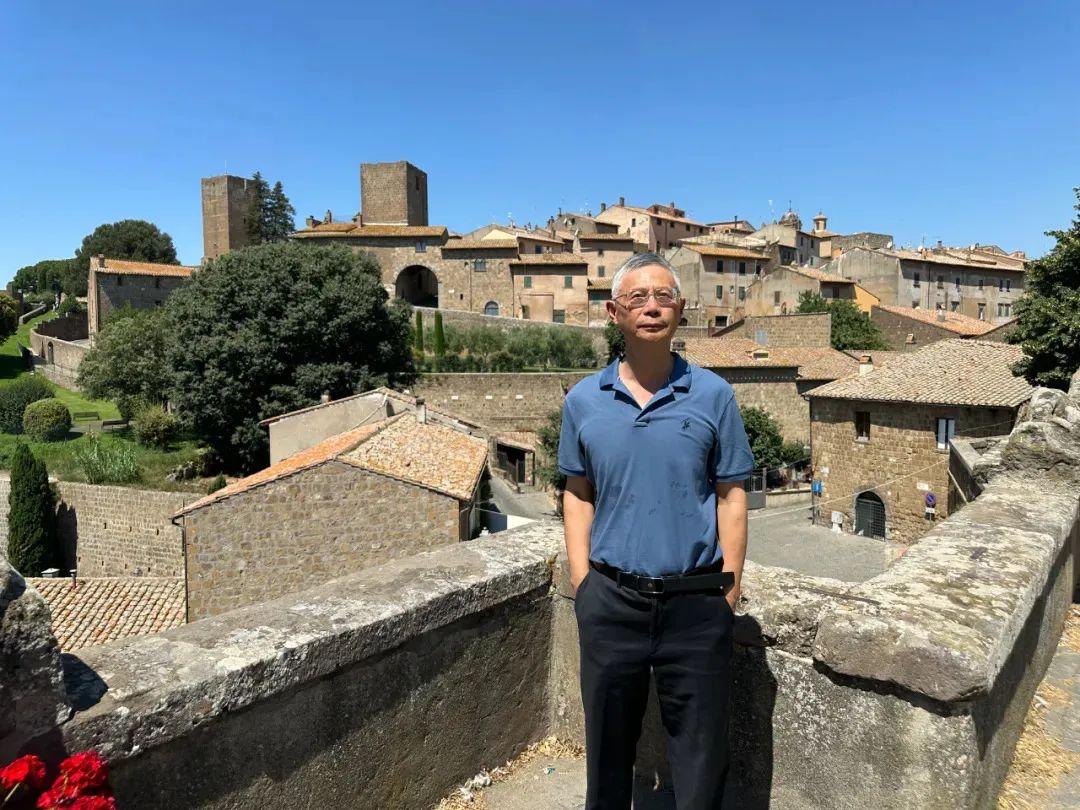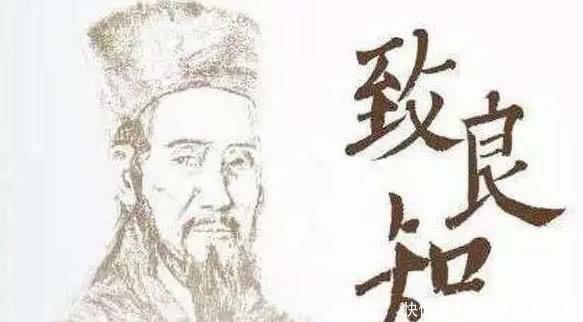德性的分析
何 俊

摘 要:德性通常被狭义地理解为美德(virtue),但它其实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概念。德性在构成形式上涉及德与性,德作为与道相对应的概念,体现了道的分殊性,而性则指向天命的普遍性。德性的内涵基础泛及万物,充满丰富性与不确定性,中国哲学史上的各种德目主要致力于分类,并以此引导人的生活,其中《易·象传》提供了一种相对系统与根源性的处理。德性的构成形式与内涵基础决定了德性至少具有四个特性,即最初的万物规定性与聚焦于人以后的哲学本体性,以及进而对人的行为进行分类所衍生的类型性,最后才是引导人的行为的可培植性。德性从自然规定性到社会教化性的内涵使其成为充满张力的概念,似更近于Essence,而非Virtue。
关键词:德性 德目 美德
德性是中国哲学与伦理学的标识性概念,典出《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德性的内涵似甚明白,按《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性是与生俱来的品质;《中庸》又以“故君子尊……”的表达,标示“君子”为主语,以“尊”为谓语,凸显对德性的价值肯定,故德性似可理解为与生俱来的良好道德品质。英译常直接译为“美德”(Virtue),似亦足佐证。但是,德性这一与生俱来的良好道德品质的核心要素似乎又是值得推敲的。南宋朱熹与陆九渊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就充分表征了其中隐含的问题。按照朱熹的理解,德性与问学是两件事,朱熹自谦道:
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尊德性,而某平日所闻,却是道问学上多。
但陆九渊不认同这一说法,他认为德性是涵摄问学的,“朱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而且,陆九渊指出,朱熹基于德性与问学的二分所表达的自谦,也不是由衷的话。陆九渊《语录》载:
或谓先生之学,是道德、性命、形而上者;晦翁之学,是名物、度数、形而下者。学者当兼二先生之学。先生云:“足下如此说晦翁,晦翁未伏。晦翁之学,自谓一贯,但其见道不明,终不足以一贯耳。”
据此,朱熹似乎是以问学来涵摄德性的。换言之,德性的核心要素在朱、陆那里是不尽相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略言之,朱熹是以问学培植德性,陆九渊是由德性决定问学。如果更就陆九渊强调的“一贯”而言,则“道德、性命、形而上者”与“名物、度数、形而下者”,似皆属德性之义,而且“道德”“性命”与“名物”“度数”尚只是列举,不足以尽言,更需用“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来囊括之。在此意义上,“德性”显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美德”。
因此,究竟如何理解德性,仍是一个必须分析的问题。本文并不想纠缠于朱陆之争,同时也不将德性等同于美德设为前提,而是希望对德性这一标识性概念进行回溯性的分析,试图给出“最好的解释推断”(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
一、德性的形式构成
所谓形式构成主要是分析概念。“德性”由“德”与“性”合成,“德”构成“性”的内涵,而德目不止于一,“性”使“德”获得一种共同性的确认,从而使“德性”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德”与“性”这两个概念在《论语》中都多次出现,表明至晚在孔子的时代,这两个概念都已是常用的概念。
只是《论语》记录孔子讨论“德”比较多,而对于“性”,据子贡讲: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者,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
为什么呢?《论语》没有直接的答案,我们只能根据相关的论说来进行“最好的解释推断”。子贡将“性”与“天道”并提,可以推知两者具有共同的性质,故可由“天道”来推断“性”。天道的含义相对比较容易确定,最表层的字义是天(自然)的运行轨迹,这一轨迹因为呈现出某种恒定性,故而更进一步地具有规律的含义,从而具有普遍而抽象的共同性。至于天的这一运行轨迹/规律是不是一个纯粹的无意志过程,正如人所周知的,《论语》给予的信息是多样而略有冲突的。比如:
(1)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
(2)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3)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1)与(2)所讲的天,虽较相似,好像都是有意志的,但如细究,也有不同。(1)更近于一种客观性的力量,(2)则完全是主观意志的存在。但是人们普遍认为,(1)与(2)都是在特定境遇中的表达,(1)是孔子在面对卫国权臣王孙贾的胁迫性暗示时讲的,(2)是孔子在宋国面临桓魋想杀自己时讲的,都属于带有情绪性的表达,只有(3)反映了孔子对天的理性认知,即认为天/自然是一个无意志的存在,天道也就是这一无意志存在的运行轨迹,其本身不具有任何价值性的含义。但事实上,人的认知,尤其是落到实践层面的,并不完全是纯粹理性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情绪的,甚至毋宁说,人在强烈情绪下的表达更足以呈现出人的整体认知的底色。换言之,孔子对于具有普遍而抽象的共同性规定的天道的判识是复杂而混合的。性与天道并列,表明在孔子及其弟子那里,性具有与天道同样的特性。作此推断,虽不中,亦不远。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凡要对某类事物的共同性给予界定,以获得一个普遍性的确定概念时,都仅仅是“为一个特殊的目的”。他以“游戏”为例说明:
我们会怎么向别人解释什么是游戏呢?我想我们会向他描述一些游戏,也许还会加上一句:“这个,以及诸如此类的,就叫‘游戏’。”难道我们自己知道得更多些,只是无法确切告诉别人什么是游戏吗?——但这并不是无知。我们不识界线是因为没划出界线。前面说了,我们可以划一条界线——为一个特殊的目的。但划了界线才使这个概念有用吗?根本不是!除非是对于那个特殊的目的。
因此可以认为在抽象概念的确定上,孔子是拥有与维特根斯坦相似的判识的,因为子贡所讲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者,不可得而闻也”并不表示孔子对性与天道“无知”,而只是表明孔子没有确切地对弟子讲什么是性与天道。仅上举数例已足以表明,孔子对天道是有所认识的,即是划了几条界线的,但它们都是在一个具体的境遇中,“为一个特殊的目的”。
事实上,即便是相较于性与天道而言,在更低一阶的概念上,如孔子自己创发而着意揭明阐扬的“仁”,他同样没有给予确切的界定,而是不断地在不同的境遇中针对不同的目的给出说明。由此可以推断,一是在“德”与“性”两者之间,“性”是比“德”更内在与抽象的概念,孔子更乐于谈论具体的“德”;二是在“德”的范畴内,孔子更乐于谈论比“德”更低一阶的具体德目,比如智、仁、勇、孝,等。这意味着,当子思在《中庸》中提出“德性”的概念时,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基于具体而众多的德目的抽象的共同性概念。这意味着,要理解德性,至少须对德目有一定的说明。
在进一步讨论具体德目以前,需要先对“德”本身予以说明。按照许慎《说文解字》:
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
德是一种获得。直与曲相对,“从直”表明德的获得是一个自然的未经干预的过程;心与物(包括了人的身体)相对,“从心”意味着德的获得是顺从自由意志的结果。至于“外得于人,内得于己”,则可以理解为德的获得可以是经由外人的传递,也可以是自觉到的;或者,经由外人传递的德,须获得自我内心的自觉与认同。
此外,既然德是一种获得,那么就意味着德必须有其获得的源头。《管子·心术上》云:“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这一阐述非常明确,且与前引《说文解字》是一致的,故大致可以确信“德者道之舍”应该是一种共识,孔子所讲的“天生德于予”是这一共识的一个具体表达。只是细究起来,作为德的源头,也许可以认为“德者道之舍”更倾向于使用“道”这个由具象的路而抽象出来的概念,而孔子更倾向于使用“天”这个概念,一个同样是具象的却包含了多重意义的概念。而且,如果就子贡使用“天道”这一概念而言,作为概念的“天”与“道”之间的区别,可谓所同甚于所异。
基于上述德是一种获得性的存在,以及德的源头是天、道或天道,因此当需要对德的共同性作出界定时,即对德性加以确认时,子思给出“天命之谓性”就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命题。在这一命题中,天道与德性之间构成了唯一性源头与分殊性存在的关系。“命”可以作动词,训作“令”;也可以作名词,如“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无论如何使用,“天命”都具有一种规定性的意涵,只是训作“令”时,“命”的规定性更偏于具有浓重的意志性的特征。作为一种规定性的意涵,天命所示的天道与德性之间构成的是一种必然性关系。但是,如果考虑到孔子对天道持有“天何言哉”的无意志的自然性质的理解,那么无论是“四时行焉”,还是“百物生焉”,在其普遍性呈现为必然性的同时,落在具体的时令节气与事物生长上,又充满了不确定性,亦即偶然性。换言之,源自唯一性的天道/天命而呈现为分殊化了的多样性存在的德性是一种必然与偶然相互作用的结果。
德性作为一种获得性的存在,而且是一种必然与偶然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德性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不具有特别的价值意涵,尤其是当天道/天命被确认为一个纯自然的过程时。在这点上,《老子》的陈述是非常明确的,第五章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万物与百姓都是天地自然所生,其因各自秉承之性(德性)而成其为自身,这一德性是没有价值意涵的,即不是西方的美德(Virtue)。儒家给人的印象仿佛与《老子》不同,儒家对于德性持肯定性的价值认定,前述子思“故君子尊德性”似乎完全表征了这一点。但是,仅从逻辑上推断,子思的这一命题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德性”持有肯定性的价值认定,而仍然可以理解为一种中性判断,即“德性”既为“天命”所予,唯有“尊德性”,方能成其为自身,故这一“尊”并不意味着对“德性”的肯定,而只是对“天命”的遵从,君子与否是在天命的认同上,至于德性本身却是中性的。
从孔子那里,可以获得这样推断的依据。孔子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德”为君子与小人之共有,德在君子那里,其德性如风,而在小人那里,其德性如草。风与草同为天地之物,并无高低贵贱的价值区别,不同处只是特性有别,草是柔软的,风是流动的,风流过草上,草即随风而偃,这也只是各顺其德性而已。概言之,由天命/天道所获得的德性,在儒家与道家的哲学中都是一个中性词。这也意味着,尽管儒家的思想重心在俗世的合理化思考中,但其前提仍然是基于对自然天道的理解,而这个理解与道家并无本质的区别。
既然德性是一个中性词,而且是源自天道/天命的分殊性存在,因此德性的确认必须通过具体的德目来完成。天地生万物,万物各得其性而成其为自身,而且万物又有各自转瞬即逝的样态,每一样态都因其所秉之性而呈现,如此,万物之“德性”便是一个无限数,人实际上面对并生存于这样的无限之中,但又必须经过类型化的处理,才可能与万物共生共长。这意味着,具体的德目必须是一个有限数,而且德目应该经由分层而呈以一种结构。
二、德性的内涵基础
这里的内涵基础就是指德目。当意识到德性是获得性的、分殊化的,同时又是具有共同性的、普遍性的概念时,为了把握德性,需要先将之悬置,通过观察与梳理具体的德目来实现。
前文提及的知、仁、勇、孝等,在中国哲学与伦理学中都是重要的德目。此外,类似性质的德目也很多,如礼、义、廉、耻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儒家的伦理规范。但是对于德性的理解,通过这些德目似乎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由下文可知,具体的德目不仅更为细碎,诸如知、仁、勇、孝、礼、义、廉、耻这些德目本身其实已是具有相当普遍性的概念;同时,选择这些明显具有美德特性的德目加以分析,既是有限的,也是未经论证的。相形之下,选择既是经过粗略分类处理的,同时又是有一定数量而形成系统的,尤其是涉及较广的德目,才是比较有效的分析对象。所幸的是,《易·象传》提供了这样的德目。
《周易》六十四卦可以视为中国哲学对于万物及其存在状态最初的类型化处理。换言之,天道被具象化为六十四种形态。依据前文的分析,在这样的具象化过程中,相应的“德性”也被天命于各自的形态。只是,存于物象中的“德性”原本是无意义的,完全分殊化了的。显然,如果人“限”“滞”于物的层级,存于人的“德性”也是无意义的,完全分殊化了的。当然,事实上,人从来没有将自己“限”“滞”于物的层级,即便是在努力去人类中心化的思想诉求中,人有别于物,仍然是一个基本的认知与事实。然而吊诡的是,人又难以逃脱物化的窘境与焦虑,这一难以逃脱不仅是在终极的死亡降临的意义上,而且是在从生到死的过程中。消解这种吊诡性的路径也许有很多,诸如各种宗教,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想,可谓不一而足。《易·象传》提供的是一条别有意趣的路径,即通过“君子以……”的句式,对存于物象中的,呈以无意义与分殊化的“德性”加以标识,引以为人之德性的母本,使各类德性以其相应的德目范导人的行为,从而扩充人的德性。由此,物与人的分隔被打通,人始终难以摆脱的物化窘境以及对自身物化的焦虑,似乎也以一种主动而有效的方式被化解。
兹请引录六十四卦口诀的前两句中的十二卦,以为例说。口诀前两句云:“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兮履泰否。”《象传》的卦解曰:
《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屯》: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蒙》: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需》: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讼》: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师》: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比》: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小畜》: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履》: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否》: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除了《比》《泰》二卦以“先王”与“后”为主语,具有特殊身份外,其余皆以“君子”为主语。这是《象传》六十四卦解的基本表达,以“君子”为主语者共五十二卦。君子是人皆可以努力的目标,以“君子”为主语充分表征了《象传》对物类之德目的观察、概括与提取,主要不是针对“先王”“后”这样的特殊人群,而是针对普通人群。由此集成的德性自然不是特殊的,而是具有普适性的。
在上述依序列举的十二卦中,标明“德”字者,有《坤》《蒙》《小畜》《否》四卦,其中《小畜》之“文德”与《否》之“俭德”标示了“德”的具体内涵,《坤》之“厚德”的“厚”可以作动词,也可以作形容词,《蒙》之“育德”则是一个动名词结构。这表明在《象传》当中,“德”是一个中性概念,这与前文根据“德者道之舍”而指出“德”是“道”的具体而分殊的存在,是一致的。作为一个中性概念,德的具体内涵还需要或可以被规定,即如《小畜》之“文德”与《否》之“俭德”。虽然“德”是一个中性概念,其具体内涵还需要或可以被规定,但由“文德”与“俭德”似乎又可以推断,“德”的中性仍然是具有肯定性的,因为“文德”与“俭德”的“文”与“俭”都应当属于肯定性的语词,似乎难以想象,或者不可能有“奢德”这样的内涵确认。但是,并非所有的内涵都如“俭”与“奢”这样具有价值完全对立的特性,“文”与“武”在内涵上是对立的,但在价值上却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同具正向性,即“文德”与“武德”都是属于肯定性的。就此而言,“德”虽然可被认为是价值中立的概念,但它的中立性更主要表现在所呈现出的括号特征,括号中的内涵固然需要或可以填入,即下文所讲的To Be,但这个括号本身仍然是具有价值属性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否则就成了“缺德”。“缺德”在今天的俗语中已是完全负面性的表达,放在“德者道之舍”的哲学意义上而言,“缺德”意味着一个事物缺乏本质上的规定性,而任何事物都应具有其自身的规定性,无论是何种规定性,否则便不成其为事物。概而言之,由“德”的中立性所呈现出的括号特征,我们大致可以推断正是这一括号特征构成了“德性”,即它是不可或缺的,但又是需要或可以被进一步内涵化的。
在此基础上,再看上述诸卦之《象传》所示的德目。首先,所有的德目都是具体的。所有的德目都指向人的具体活动,而不只是抽象的观念。其间有所不同的是,《乾》《坤》两卦的德目更具有普适性,“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可以适用于每个人的所有行为,只是“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两者彼此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性,或者说是相反的指向,“自强不息”是针对自我的要求,而“厚德载物”是针对他人的态度,尽管同样也是针对自我的要求,但这种针对自我的要求是呈现于对象性的外部事物的。显然,《乾》《坤》两卦的特性是由《易》的世界观决定的,即阴阳二气构成了一切事物存在的物质与能量基础。然而明确《乾》《坤》德目的这种对应性,足以表明在根源性的中国哲学《易》的德性观念中,无论是在发生论意义上,还是在本体论意义上,作为万物之基础的本体,阴阳二气的德性即是分殊了的,而且是需要彼此配合的。当然,在《易》学中,阴阳之上还有“太极”,但“太极”就是天道/天命,必见之于阴阳才有具体的万物,此即《易·系辞》所谓“乾坤其易之缊”“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换言之,论德性必须落在乾坤,必然是呈现出分殊了的对应性。
其次,《乾》《坤》以外的十卦,无论是针对“大王”与“后”代表的特殊身份者,还是针对“君子”这样的广泛人群,所有德目都是非常具体的。每一德目对应于具体的事项,近乎人在各种事务中都应当呈现以相对应的德。如试作分类,这些极度分殊化呈现出的德可大致被归入某种类别中,比如前述《小畜》卦的“文德”、《否》卦的“俭德”。显然,《象传》所列德目并没有这样强烈的分类意识,而更呈现为完全分殊化的更具体的德目。比如,《屯》卦之“经纶”、《讼》卦之“作事谋始”,应可归入“智(知)德”;《蒙》卦之“果行”,可归入“勇德”;《师》卦之“容民畜众”,可归入“仁德”;而《比》卦之“建万国,亲诸侯”、《履》卦之“辩上下,定民志”、《泰》卦之“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否》卦之“不可荣以禄”,则兼含知、仁、勇之德,或二,或三,难以归于一德。
尤有意趣的是,上述诸卦所示之德,尚可以归入人之精神内涵的德,而《需》卦标示的“饮食宴乐”,似乎已近乎人之生理内涵的德了。诚然,人之“饮食宴乐”早已属于社会性的行为,但不得不承认,“饮食宴乐”的核心内涵终究还是人之自然性的行为。
上述的分析虽然只是取诸《易》的前十二卦,未及六十四卦全部,但所取十二卦是依序所取,并没有任何主观意向,因此上述的分析可以推及整个六十四卦所标示的德目。由此可知,六十四卦尽管已是经过了对无比繁复的人类行为的分类处理,但是由此而提炼出的德目仍然是极度分殊化的。这种分殊性不仅限于人的社会行为与精神内涵,而且涵摄人的自然生理行为;同时,这种分殊性不仅呈现于具体的行为,而且是一切事物的发生与基础。这意味着,构成德性的内涵基础的德目是极其丰富的。
三、充满张力的德性
德性的形式构成与内涵基础决定了德性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概念。在形式构成上,“德”完全是具体的,“性”则寻求某种共同性,二者之间已然形成一种张力。在内涵基础上,德目从根源性上已决定了其以分殊化的状态呈现,而从丰富的德目中确定它们的德性,决定了德性因将这种丰富性纳入自身,张力亦自然随之形成。为了更充分地论证德性充满张力的特质,基于上述分析,这里进一步对德性做一个综合性的申说。
德性是指全部存在事物的各自规定性,这是德性最表层的含义。如前所述,“德者道之舍也”“天命之谓性”这些命题清楚地表明,德性这一复合概念是指向分殊化存在着的形形色色事物(现象)的各自规定性,万物皆因这种内在规定性而成其为自身,凡物皆有其自性,而且这种种事物都不是静态的,而是始终处于演化中。因此,由于这样存在的事物是一个无穷数,相应的德目及其德性也自然是一个无穷数。在这个意义上,德性固然可以在哲学的意义上加以理解,但似乎更适合被理解为一个自然概念,故不妨以自然的规定性来界定德性的第一层含义。
同时,在全部存在事物的各自规定性的意义上,德性并非为人所独有。《中庸》所言“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这个“尊德性”可以按照传统与通常的训解,专门针对人而言,释为尊崇人的内在规定性,但并不能排除尊崇所有事物的内在规定性的解释。《中庸》此句所在之章的开头说:“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发育万物”的前提无疑必须尊崇万物的内在规定性。这也佐证了上述所揭明的作为自然规定性意义的德性。诚然,德性因其聚焦于人,更多地作为伦理学的概念被加以使用,而当如此被使用时,德性便由一个自然性的概念转向一个哲学性的概念,因为只有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时,德性才足以成为一个由针对万物而提出的具有普遍性的、共同性的概念,并进一步衍生出它的伦理学属性,成为一个伦理学概念。当然,哲学概念与伦理学概念是可以兼容的,但彼此还是会有中心的不同与边界的区分,各有不同的意涵。
这里先说作为哲学概念的德性,这也可以被视为德性的第二层含义。德性虽然在最表层的意义上指所有存在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但是这一呈现以无穷数的存在既不是混乱无序的,也不是缺乏统一性的,相反,它们拥有唯一的共同源头,即天道/天命。这种唯一性与共同性,既保证了万物的有序与统一,更明确了天道/天命在发生论与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由于天道/天命依循发生论的逻辑在形成万物及其演化的过程中,本体相应地融入万物而成为各自的内在性,因此,德性除了最表层的万物内在规定性的含义外,也具有本体的含义。
德性既是多,这是显见于表的;又是一,这是隐晦于内的。中国哲学高度强调的道器不二、显隐无间,在德性概念中获得了充分彰显。作为表象存在的多,德性随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或事物因其德性的变化而变化,德性是活动的;作为隐晦于内在的一,德性根源于天道,尊崇于天命,是静止不变的。毫无疑问,无论着眼于显见的、变化的,还是隐晦的,静止的,所见不同,相应的行动也自然不同,《损·彖传》“损益盈虚,与时偕行”与《系辞》“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可为注脚。德性既然意指全部事物的各自规定性,那么就不属于一个共同性的概念;即便是限于人的范围来使用,人固有共同性,但各人皆有自己的规定性,德性仍然不属于一个共同性的概念。这意味着无论在哲学还是在伦理学的论域中,德性指向的都是分殊化存在着的现象,而不是现象背后的共同性。然而,如前文所述,在中国哲学中,“德者道之舍也”“天命之谓性”,所有事物的规定性都是本体意义上的道/天命的分殊性存在,即中国哲学中最具独特性的道器不二、显微无间。因此,德性虽然是指向分殊化存在着的形形色色现象,但此现象同时呈现出形而上的本体,这个本体是唯一的、共同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如强取西学的概念来讲,或近于being与Being,前者是存于当下转瞬即逝的“此在”,后者是“在成其为在”的“本体”。故德性兼涵表象与本体,固执一端是不足取的。
德性的第三层含义是伦理学的类概念,这也是德性最被理解与使用的概念。作为伦理学概念,德性因其对人的行为的指称而被使用。在这种使用中,德性本身虽然仍是一个普遍的共同性概念,但事实上是被细化成类概念来使用的,即前述提及的知、仁、勇、孝、礼、义、廉、耻,以及诸如列举《象传》诸卦所引及的“文德”“俭德”等。为什么德性在实际使用时会呈现以类概念的形式呢?如《象传》“君子以……”的句式所示,落于人的德目源自对自然现象的兴发感知,自然现象既纷繁又多变,人的兴发感知也随时随地千差万别,但人的行为及其背后的理据必须是相对稳定的,才足以范导人的行为,这是作为伦理学意义上的德性概念呈现以类概念的根本原因。
此外,人的行为本身是中性的,故德性并不具有价值内涵,此正如自然现象,无论是风和日丽还是狂风暴雨,其本身并无价值内涵。这些自然现象之呈现出某种价值属性,完全是因为人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需求为标准而赋予自然现象以各种价值属性,并进而引以为人自身的属性而加以培植。但是,在且仅在这个意义上,德性仍然还是中性的,如前文所及《象传》解《需》卦所谓“君子以饮食宴乐”。“饮食宴乐”本身是一自然行为,其德性是中性的,只是这一中性的饮食行为有着“民以食为天”与“病从口入”这正反两方面的价值属性,故“饮食宴乐”这一中性的德目便含有它更具深意的价值引导,此正是整个《需》卦所要揭明的。换言之,当人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需求为标准而赋予自然现象以各种价值属性,并进而引以为人自身的属性而加以培植时,德性已被确认为是“好”的规定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性便与美德(Virtue)同义。
德性这一因人对自然的兴发感受而引以为自性的特质,即《象传》的“君子以……”句式,使得德性具有了第四层含义,姑且强名之可培植性。根据《象传》“君子以……”的句式,德性的这一可培植性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即向万事万物开放。天命所赋予的自性只有在这一向外部世界始终开放的过程中才真正形成,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借用西学的表达,To Be或能近于表达德性的可培植性含义。
按《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德性固然自始获自天命,但此先天禀赋需要后天培植,这个培植分为两个过程或两种状态,前者为“率性”,是先天禀赋所得自性的自我生长,后者是“修道”,是“率性”过程中的纠偏。这里隐含着一个问题,这两个过程在逻辑上虽然具有关联性,“率性”在前,“修道”在后,但后者并不是必需的。如果“率性”是顺利有效的,那么“修道”自然可以免去;反之,“修道”便是非常重要的过程。无论如何,承认自性的先天禀赋是前提,否则一切无从谈起;而且,培植仍是必需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不是必然需要校正纠偏。
至此,引言中论及的朱陆之争便不难理解。朱子显然认为“修道”这个校正纠偏的过程是人所难免的,甚至是人所必需的,且他更强调德性的可培植性,故重心落在格物、落在“道问学”上,尽管他不否定德性的先天固有。但在象山看来,承认德性的先天禀赋更为重要,而一旦对此有所自觉,德性的可培植性就是一个自然展开的过程,人在面对事物时自然对事理有所明察,刻意的“道问学”往往适得其反,徒费精神,学不见道。
引言中说明,本文的论题虽由朱陆之争起,但问题却不是分析或调停朱陆,而在于对德性这一标识性概念进行回溯性的分析,试图给出“最好的解释推断”。因此,经由上述的分析与综合,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德性这一概念在内涵上不仅具有不同的层面,而且每一层面涵摄着不同的指涉,从而使得德性概念具有高度的丰富性;由于这些丰富的含义各有特殊的指涉,故又使得彼此之间充满张力。如果限于德性的某一含义来范导人的行为,实际上都是不充分的。只有在具体的境遇中恰如其分地彰显相应的德性,才是德性的最好呈现,相应的德才足以成为“至德”,而且这一“至德”是始终变化的,“至德”也意味着要始终保持自身的恰当性,亦即“时中”。故孔子的感慨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无疑是对充满张力的德性的深切体会。也许正因为基于这样的理解,德性从自然规定性到社会教化性的内涵使其成为充满张力的概念,或更近于Essence,而不是Virtue。
原文刊登于《道德与文明》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