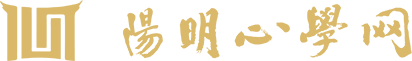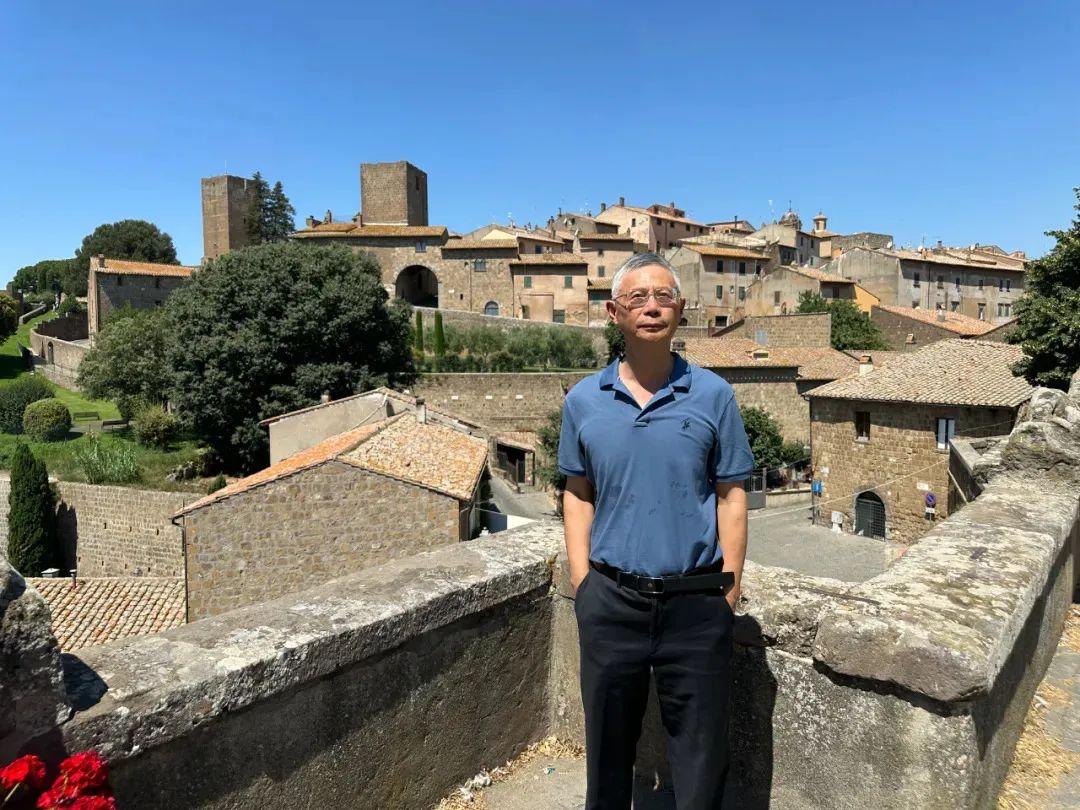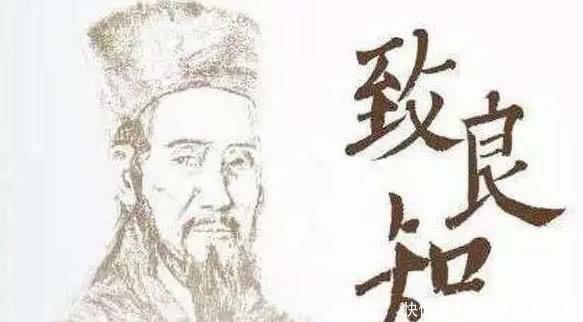心知、灵明及其与气的关系问题:以阳明学为中心的讨论
翟奎凤
南京大学哲学学院
本文来自《哲学动态》2025年第6期 “中国哲学的话语与形态”栏目
[摘要]阳明晚年多次以灵明论良知,并以气言万物之一体。对于良知与气的关系,学界尚未深入讨论,也未注意到禅宗的灵明、灵知思想对阳明学的潜在影响。阳明强调良知灵明与气的一体性,甚至认为良知是宇宙造化之精灵。王畿、邹守益等都非常看重阳明晚年的良知灵明论,并视此为儒家千古一贯之道脉。王畿提出“一念灵明”,又以灵气诠释良知,发展了阳明的良知灵明论。良知是一种灵气,并不等于把良知降格为形而下之存在;灵气论突显了阳明学良知思想的宇宙论、生生论面向,这是其有别于禅宗灵明思想的重要特征。在阳明学看来,灵明不离气,同时又对气有超越性和主宰性。实际上,此种看法对晚明心气关系的相关讨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灵明;良知;气;阳明学
阳明晚年多次以灵明论良知,同时又以气言万物之一体性和贯通性,这就涉及良知灵明与气的关系问题。受阳明影响,其门人也多以灵明论良知,甚至视此为儒门千古一贯之道脉。阳明门人有的主张灵明即气之灵,有的则强调灵明对气有超越性、主宰性。灵明与气的关系问题,与神气、心气、理气、道气关系有着密切关联,这是一个非常古老同时又讨论不断的根本性哲学问题。近年来,陈来、吴震等学者颇为关注阳明晚年思想。陈来指出,“阳明后期讲学多用灵明,它与明觉类似,都是在不同功能上用来代替心的主体概念”(陈来,2020年,第48页),“阳明后期在界说良知时,是很强调‘灵明’作为良知属性的,表示良知既是明的,也是虚的,又是灵的”(同上,第49页)。实际上,“灵明”一词在唐代佛学、宋元道教中已有较多使用,阳明所言“灵明”与其有相通处。但目前学界结合佛道背景来讨论阳明及其门人的良知灵明说的研究还较少。此外,阳明也使用与灵明意思相近的“精灵”一词。陈立胜曾通过“精灵”一词对阳明良知学有深刻揭示。(参见陈立胜)相对而言,阳明及其门人讨论良知时使用“灵明”一词的频率更高,更值得关注。
一 唐宋金元时期佛道儒论灵明与心知
从现有文献来看,先秦文献中并未出现“灵明”一词,较早在本体论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当属唐代高僧宗密。宗密对禅宗、华严宗思想有综合继承,形成一种独特的华严禅思想。元和五年(810),唐宪宗向华严四祖澄观请教如何理解华严宗所说的“法界”,澄观说:“法界者一切众生之本体也,从本以来,灵明廓彻,广大虚寂,唯一真境而已。”(《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卷二十一)澄观这里以“灵明廓彻”来形容本体性法界,此法界也是心性本体。传统佛学多视“知见”为无明之本,而慧能弟子神会把“知”转化提升到本体的高度,提出“知之一字,众妙之门”(《无异元来禅师广录》卷一)的惊人论断。宗密叙述其师神会的禅学思想时说:“妄念本寂,尘境本空。空寂之心,灵知不昧。即此空寂之知,是汝真性。任迷任悟,心本自知,不借缘生,不因境起。知之一字,众妙之门。”(《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二)这里的“空寂之知”即灵明之知。由此可见,宗密也继承了澄观的华严思想。
宗密提出空宗与性宗有十大差别,其中第二条是“空宗一向目诸法本源为性,性宗多目诸法本源为心”,“目为心者”“良由此宗所说本性,不但空寂,而乃自然常知,故应目为心也”;第三条是“空宗以诸法无性为性,性宗以灵明常住不空之体为性”;第四条是“空宗以分别为知,无分别为智,智深知浅。性宗以能证圣理之妙慧为智,以该于理智、通于凡圣之灵性为知,知通智局”。(参见《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下一)性宗所说之性即是心,此心空寂而灵明常知。同时,此“知”高于“智”,智为圣人之果位,而知则通于圣凡。宗密“知通智局”之说源自澄观,是对传统“智高于知”认识的颠覆。澄观对比了“佛境界智”与“佛境界知”的不同:“智即能证,知即心体,通于能所。”(《华严经行愿品疏钞》卷二)他还引述神会“知之一字,众妙之门”来说明这个道理。神会、澄观都主张心性本体即寂即知、寂知合一,宗密对此予以继承和发挥。总而言之,从神会、澄观到宗密,都强调寂知、灵明之知。
宗密特别区分了灵明与日月光明:“若但云明,未简日月之类,故云灵也,意云心之明者其在无法不知而无分别,无法不现而无差别,幽灵神圣,寂然洞然,故曰灵明。”(《圆觉经大疏钞》卷一上)宗密认为,此灵明非经验性感官之明,而是一种神灵之明。他还会通易学来阐扬佛理:“元亨利贞,乾之德也,始于一气;常乐我净,佛之德也,本乎一心。专一气而致柔,修一心而成道。心也者,冲虚妙粹,炳焕灵明,无去无来,冥通三际,非中非外,洞彻十方,不灭不生。”(《圆觉经·序》)这里宗密以“元亨利贞”(气)、“常乐我净”(心)相对,同时以灵明论心。就此而言,灵明之心非气,对气有超越性;此不生不灭的心是先天的本体灵明,非后天意识心。“灵明”一词在宗密著述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他还说:“觉本无念,见念既乖。性本灵明,迷照亦失······夫觉体灵明,不唯寂灭。今灭惑住寂,岂得相应。”(《圆觉经略疏注》卷下二)“六道凡夫、三乘贤圣根本悉是灵明清净一法界心。性觉宝光,各各圆满。”(《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下二)在他看来,灵明是众生本觉之性,“一切众生无不具有觉性,灵明空寂,与佛无殊······灵灵不昧,了了常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以空寂为自体,勿认色身。以灵知为自心,勿认妄念”(《景德传灯录》卷十三)。宗密还常用“灵知”“灵心”“灵性”“灵觉”“灵灵一心”等语词,强调本心即寂即觉,有着灵明的功用。方立天说:“宗密认为,代表印度佛教的空宗讲的心性是不觉、无知的,是诸法无性为性,而中国佛教的性宗讲的心性是本觉、有知的,是以灵明常住不空之体为性。心性本觉说是肯定心性觉悟不是可能而是现实的,是不需要经过修持就本来具有的。宗密所说的心性具有现实灵知不空之体的思想,实为隋唐时代中国化佛教宗派天台、华严和禅诸宗所共有,并成为这些宗派的理论基础。”(《方立天讲谈录》,第339页)可以说,此种以灵知之性、灵明常知之心为真如本体的性觉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阳明的良知思想。
北宋初年晁迥对宗密很推崇,“予素爱重唐圭峰禅师宗密,所述法要之书,尤为详备”(《法藏碎金录》卷八)。在宗密的影响下,晁迥在其著述中也常用“灵明”一词:“至虚至静是其体,至灵至明是其用。千经万论,不离于此。能深入于虚静,必渐显于灵明。”(《道院集要》卷二)此以虚静为体、灵明为用的思想,与宗密所说“寂是知之自性体,知是寂之自性用”(《圆党经略疏钞》卷一)是一致的。晁迥还说:“众生之心,本有空寂安乐之体,臻其极者,此名涅槃;本有灵明照了之用,臻其极者,此名菩提。”(《法藏碎金录》卷一)这也是以涅槃空寂为体、灵明菩提为用。晁迥又说:“气质有衰,物数之常也;灵明不昧,天真之本也。知常达本,始可与言道已矣。”(《昭德新编》卷上)“有名有色,随造化而迁革;无色无名,亘古今而灵明。”(《法藏碎金录》卷一)在晁迥看来,气质为形而下、为身,灵明为形而上、为心,道贯通身心、形上形下。灵明即佛性、觉性,作为天真之本有着不生不灭的永恒性,对形气物来说具有根本性。南宋北山法师可旻在诗中说:“混然凡圣本同途,一点灵明体一如。只为妄情随物转,至今颠倒未逢渠。”(《乐邦文类》卷五)这是“一点灵明”一语的较早出处。元代僧人释大欣说“灵明之性,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亡,不以圣而增,不以凡而减”(《蒲室集》卷十三),此灵明之性即佛性,圣凡同等,无有差别。元代僧人释文才说“本觉灵明,无法不照,故曰遍知”(《肇论新疏》卷中),“神妙灵明,谓般若也”(同上)。又说:“此心从本已来,清净无染离喧扰之相,故曰寂也;具灵明觉知,故曰照也。圭峰云:‘心寂而知,目之圆觉’。”(同上)“圭峰”即宗密,灵明在此表示心性并非死寂、顽空。可见,宗密的灵明、灵知思想在宋元时期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
金元时期的全真教亦喜言“灵明”“一点灵明”。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在其丹道诗中说“元本灵明便惺惺”(《重阳全真集》卷十二),“一点灵明归静界,圆光里面转金轮”(《重阳全真集》卷一),“拥出灵明,一颗神珠衮颠倒”(《重阳全真集》卷十一)。全真教融合了佛禅思想,这里的灵明近于佛教所说佛性、心性本体。在王重阳的影响下,全真道士也多言“灵明”。如谭处端说“本来真性是玄机,只在灵明悟得时”(《水云集》卷下),刘处玄说“别有铅房汞库,一点灵明是主”(《仙乐集》卷一),尹志平说“归根复命性灵明”(《葆光集》卷下),王玠说“此一点灵明,无形无相,无古无今,贯石透金,本无所说”(《远真集》卷中)。以上多是从主体心性的角度讲灵明,强调灵明是恒生不灭的本性。全真道士常言“一点灵明”,后来阳明及其弟子王畿等也用这个词,大概是受到全真道的影响。
元代道士李道纯也多言“灵明”。他说,“太初一点,本灵明,元自至纯无杂”(《中和集》卷六),认为“一点灵明”是“真种子”。“或谓人从一气而生,以气为真种子。或谓因念而有此身,以念为真种子。或谓禀二五之精而有此身,以精为真种子。此三说似是而非。”(《中和集》卷三)他反对以气、念、精为“真种子”,强调“真种子”只能是至纯无杂的灵明。李道纯更多从本体、本根的角度讲灵明的先天性。其弟子苗善时也说:“一点灵明,圆混混,活泼泼,无心为而为,时止时行,以辅万物之自然。”(《玄教大公案》卷上)显然,此灵明也就是道的体性。灵明为道的体性,也是心性之本然。他还说:“心虚则元炁冲融,炁息则灵明朗彻,非即非离,互体妙用。”(《玄教大公案》卷下)灵明即本心,这是讲心气相依、不一不二。苗善时又说:“一点灵明无昧,性也;一点元气常调,命也。性无命,则无依倚,亦不能安。止命无性,则不冲融,亦不能固密。二物混融,一真玉莹。”(《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卷二)“元气常调”即上文所说“炁息”,通过这一工夫,就能朗现灵明。灵明为性,元气为命,性命双修即达到灵明心性与元气浑融的状态。灵明之性虽不能离开气,但李道纯、苗善时强调灵明之性更为根本。
两宋理学家讨论灵明较少,北宋五子罕有论及,唯有“子厚曰:‘勿忘者,亦不舍其灵明,善应之耳。’子曰:‘存不舍之心,安得谓之灵明?’”(《河南程氏粹言》卷二)张载“不舍其灵明”所要表达的意思,应该近于佛家所说“不昧其灵明”之义。二程大概是强调内心灵明之自在性和本然性,但“不舍”有刻意之嫌,不大自然。至南宋,朱子似仅一处用及“灵明”一词。他在《答陈正己》的信中说:“上为灵明之空见所持,而不得从事于博学笃志、切问近思之实。”(《朱子全书》第23册,第2558页)这里所说的“灵明之空见”有批评佛家的意思。
宋元之际的朱子门人后学,对“灵明”一词使用较多。黄震说,“心者吾身之主宰,灵明广大,与造化相流通,所以治事而非治于事,惟随事谨省则心自存”(《黄氏日抄》卷八十六),强调灵明之心对身体和事务的主宰性。熊禾说:“人之一身与天地相似:无极、太极,吾其性;二炁、五行,吾其体;而其中一点灵明,炯然不昧,则合性与知觉而谓之心也。”(《勿轩集》卷三)他以灵明为心之特征,这大体上也体现了朱子的意思。
陆九渊常说“此心之灵,此理之明”(《陆九渊集》卷七),但他基本上没有使用“灵明”一词。在陆九渊启发下,杨简多次使用“灵明”一词:“神魂之妙,无所不通,广大灵明,唯昏故小故拘。”(《杨简全集》第5册,第1484页)曾从学于杨简的袁甫使用“灵明”一词的频率更高,如“此心灵明,固不以生死隔也”(《蒙斋集》卷十五),“一性灵明,与天地并,亘万古不可磨灭者”(《蒙斋集》卷十六),“夫其所以有是灵明不昧者,皆天命之性也”(《蒙斋中庸讲义》卷三)。可以看出,袁甫这里的心性是不分的,灵明是心也是性,有着超越时空的永恒性。
大体来说,唐宋时期“灵明”一词在佛道论学中使用较为广泛,而这其中宗密的作用尤为突出,他关于“灵明”系统化、哲理化的论述对后来的道教和儒学都有较大影响。
二 灵明与阳明晚年的大良知学
良知是心的灵明状态,同时也是性、天理的本然灵觉。阳明说:“性之虚明灵觉,即谓之良知。”(《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5册,第1632页)这样良知是心体,也是性体。1523年,52岁的阳明在答舒国用的信中说:“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惧,惟恐其昭明灵觉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于非僻邪妄而失其本体之正耳。戒慎恐惧之功无时或间,则天理常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无所亏蔽,无所牵扰,无所恐惧忧患,无所好乐忿懥,无所意必固我,无所歉馁愧怍。”(《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1册,第203页)这里所说“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可以看作先前“知是理之灵处”的发展;“昭明灵觉”也可以视为“灵明”一词的展开。而“灵觉”一词宗密也多有使用,如“此心是一切众生清净本觉,亦名佛性,或云灵觉”(《禅门师资承袭图》)。其后,阳明54岁时说:“明德者,天命之性,灵昭不昧,而万理之所从出也。”(《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1册,第267页)55岁时说“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同上,第78页),“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同上,第92页)。这样良知是天理、天命的灵性显现或灵明自觉,昭明灵觉、灵明之心就成为一种本体。而作为形而上本体之实存的“天理”就不仅如程子所说的“冲漠无朕”(《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朱子所说的“净洁空阔”(《朱子全书》第14册,第116页),同时也是一种有灵觉和明觉之性的灵明或灵知。这类似宗密所论本体,不但“空寂”,而且“常知”,是“灵明空寂”与“了了常知”的统一。
据《阳明先生年谱》所载,阳明借助《大学》大发“万物同体之旨”(《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4册,第1299页)。陈来认为,“万物一体的思想在阳明先生晚年良知学体系里面,所引起的一种变化,或者说对阳明先生晚年思想体系的完善所发生的一个作用,居越以前是没有的”(陈来,2019年,第46页)。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集中体现在《答顾东桥书》《答聂文蔚书》中,同时也体现在一些问答语录中。如阳明在与学生论及人与草木、禽兽如何能够一体时,提到《礼记·礼运》所说“人者,天地之心也”[1],认为人心“只是一个灵明”,阳明还接着发挥说:
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传习录》卷下)
充塞天地的“这个灵明”侧重指宇宙本体,是遍在一切的天地之心,而“我的灵明”是主体之心灵,同时又是天地灵明的发窍。灵明之心充塞天地,并且能主宰天地鬼神。对此主宰,我们不能生硬地认为人心能操控天地、鬼神,从后文所说仰高、俯深来看,此主宰主要是指认知与辨别的能力。灵明之心与天地万物是一气流通的,相互之间没有间隔,相互依存而不可分离。吴震认为,“我的灵明”即“我的良知”:“阳明无疑是在宣称,良知才是宇宙万物、天地鬼神之所以存在的最终依据,质言之,良知也就是宇宙本体······天地万物之所以是一种对人敞开的意义世界,其依据端在于‘我的灵明’而非其他。”(吴震,2011年,第137页)灵明与天地万物一气流通,它以贯通一切之气为载体而充塞天地。
阳明晚年居越期间,江苏靖江人朱得之(字本思)前来问学,直到阳明去世的前一年才离开。朱本思提出,若人有虚灵、灵明之心才有良知,那么像草木、瓦石之类没有虚灵之心,是否也有良知呢?这有点类似禅学中“狗子是否有佛性”之问。阳明对此回答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传习录》卷下)天地万物与人同此一气、一体相通,在此一体中,人心一点灵明又是其发窍最精处。这一思想,在朱本思所录另一段阳明语录中也有相近表述:“今夫茫茫堪舆,苍然隤然,其气之最粗者欤!稍精则为日月、星宿、风雨、山川,又稍精则为雷电、鬼怪、草木、花卉,又精而为鸟兽、鱼鳖、昆虫之属;至精而为人,至灵至明而为心。······所谓心者,非今一团血肉之具也,乃指其至灵至明、能作能知者也。此所谓良知也。······若其本体,惟吾而已,更何处有天地万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5册,第1608—1609页)朱本思在这段记录后还有一段跋语:“此乙酉(按:1525年)十月与宗范、正之、惟中闻于侍坐时者,丁亥(按:1527年)七月追念而记之,已属渺茫,不若当时之释然,不见师友之形骸、堂宇之限隔也。”(同上,第1609页)这里阳明把万有存在视为一个由粗到精的递进序列,而“至灵至明”的人心是最高端。这与前段所说“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意思相近,当是阳明在同一时期说的话。笔者认为,相对来说,《传习录》所记当更接近阳明本意。从“最粗”“稍精”“又精”,到“至精而为人,至灵至明而为心”,阳明这里的人心有点像金字塔顶的宝珠,金字塔托起、支撑起灵明,而灵明又照耀着金字塔。这有点进化论的意味,容易让人误解好像进化到人心才有此灵明,模糊了良知灵明的本体论意义。
对此,我们或可结合黑格尔的思想来诠释,即草木瓦石等自然物是绝对理念的外化。贺麟在诠释黑格尔哲学思想时说,“‘自然’乃代表精神之外在化,乃是顽冥化的不自觉的精神”(贺麟,第152页),而“精神克服了异己化,又回到了理念自身,从而达到了自觉的理念。所以精神称为自觉的理念,或现实的理念。理念是无血肉的抽象的纯本质,自然是潜在的,不自觉的纯本质的理念,精神是显现出来的自觉的理念”(同上,第235页)。邓晓芒也指出,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比如说石头)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实际上灵性也包含在里头,只不过是被压制了······在自然界里面,精神还在沉睡,但是它有这种能力,并且这样的能力并不是由外界输入的,而是这些东西本身内在就有的”(邓晓芒,第61页)。自然界朝着精神维度、灵明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向演化,直至人的精神实现理念的自觉。这与阳明以良知为天理之昭明灵觉状态有些类似。在阳明看来,“堪舆”大地是最粗的,稍精为日月,又稍精为雷电,又精为鸟兽,至精为人。这可以看作灵明精神程度越来越高的演化状态。我们也可以说自然之气有灵明、精神性。在黑格尔那里,自然物的精神潜质归于绝对理念(上帝),而阳明以心为气的至灵至明状态,这内在包含着天理,因此可以说是心气之灵明使得天理昭然明觉。天地灵明作为本体是本有,其与气的结合又展开、呈现为一种进化趋向,至人心之灵明方使得灵明本体能够自觉,使潜存成为现实。
良知灵明与气的关系问题,一定意义上可以转换为性与气的关系。性气、理气关系,对应身心关系。性理、良知、灵明在一个层面,身体、气、物在一个层面,构成一种形而上下之关系。理学家普遍强调性理良知更为根本,对后者有主宰、支配性作用。欧阳崇一曾问:“寻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无事亦忙,何也?”(《传习录》卷上)阳明说:“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同上)这个主宰或“天君”,对天地而言是天理,对人而言就是良知。天理对天地气机、良知对一身之气有主宰性。对阳明这句话,泰州学派方学渐加按语说:“流行者气也,主宰者理也,知理之为主,则知从事于气者之非学矣。”(《心学宗》卷四)阳明还说:“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若无真己,便无躯壳,真是有之即生,无之即死。”(《传习录》卷上)这里所说的“真己”“主宰”即良知、灵明。当然,阳明基于其圆顿思维,反对将二者分得太开,他常用“一也”之表述来强调存有之圆融性、一体性[2]。当有人问及仙家元气、元神、元精之说,阳明回答说:“只是一件: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传习录》卷上)这是阳明中年所说。晚年阳明又论及此,并把此“一件”规定为“良知”:“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1册,第68页)阳明把精、气、神统一到良知上,将三者视为良知本体在不同角度的功能表现,由此也表明良知灵明之根本性。阳明晚年还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传习录》卷下)这段话也让我们联想到《庄子·大宗师》中对“道”的论说:“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阳明所说“与物无对”的“精灵”,类似于《庄子》所说本体之“道”。《管子·内业》说:“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与“形”相对的天出之“精”也可谓是一种“精灵”,是人生命活力的根本。“精灵”遍布宇宙,生成万物,是万物生命力的根本。失去“精灵”,万物就会死亡。人在安静、心平气和的状态下,精神活动合于“道”的规律,“精灵”会向人聚集。“精灵”显现为意识活动,才有了世界万物如此这般向我们展开。“精灵”也可以说是一种灵明,良知精灵说就把良知提升到宇宙论层面,而此种良知可谓真正的“大良知”[3]
三 王畿对阳明良知灵明思想的发展
阳明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以灵明论良知,这对其门人影响深远。阳明去世时,大弟子钱德洪在讣告中说:“斯道晦冥几千百年,而昭明灵觉之体终古不磨,至吾夫子始尽发其秘。”(《徐爱 钱德洪 董沄集》,第216页)终古不磨的“昭明灵觉之体”即良知,钱德洪视此为阳明所揭示的儒门“秘”教,而“斯道晦冥几千百年”则视阳明超迈宋儒、直接孟子!大弟子邹守益与王畿也非常看重阳明的良知灵明说,两人曾在“玄谭”这个地方聚谈三日。邹守益说:“别去发明师门灵明一脉,可谓恳到。吾辈果能从灵明不昧自戒自惧,日用人伦庶物,无众寡小大,罔敢瞒过,更无歇手处,亦无换手处,不患不笃实光辉。”(《邹守益集》上册,第635—636页)两人分别时还互赠诗作,邹守益在《玄潭次龙溪见赠》一诗中说:“灵明一窍师传辟,瑟僴新功病骨慵。”(《邹守益集》下册,第1333页)可见,钱德洪、邹守益、王畿等大弟子都把良知灵明说视为阳明学的重要精神血脉。
相对来说,阳明弟子中谈论良知灵明最多、最为深刻的是王畿,他对阳明的灵明良知论作了充分展开与发挥。王畿在致裘鲁江信中说:“兄自嘉靖丙戌闻学已来,深信良知灵明变化为千圣传心正法,时时只从人情事变上理会。”(《王畿集》,第455页)这里他将良知灵明视为阳明所发明的儒门心法。王畿视“一念灵明”为阳明之真脉、儒家之道脉,“一念灵明,直超尧舜,上继千百年道脉之传,始不负大丈夫出世一番也”(同上,第68页),“千古圣学只从一念灵明识取,只此便是入圣真脉路”(同上,第451页)。他在解释“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时说:“道无生死,一念灵明,照彻千古。”(《王畿集》,第415页)可见,王畿所说“一念灵明”类似一种顿悟,在瞬间(“一念”)证悟永恒。他又说:“先师提掇良知二字,乃是千圣秘密藏。虞廷所谓‘道心之微’,一念灵明,无内外、无寂感。吾人只是不昧此一念灵明,便是致知;随时随物,不昧此一念灵明,便是格物。”(同上,第681—682页)“不昧此一念灵明”即不昧此良知,灵明即良知,格物致知即不昧此良知灵明。王畿也多次从灵明的角度讨论格物致知,如“致知者,致不学之知,是千古秘密、灵明之窍;格物者,格见在之物,是灵明感应之实事”(同上,第229页)。
此外,王畿还结合易学来论良知灵明:“一念灵明,从混沌立根基,专而直,翕而辟,从此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是谓大生广生,生生而未尝息也。”(同上,第167页)根据《周易·系辞上》所论“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此处“专而直”“大生”实际上指乾道,“翕而辟”“广生”则指坤道。就此而言,灵明相当于统摄乾坤于一体的太极。但王畿又说:“《易》曰‘乾知大始’,良知即乾知。灵明首出,刚健无欲,混沌初开第一窍,未生万物,故谓之大始;顺此良知而行,无所事事,便是‘坤作成物’。”(同上,第213页)这里他又以灵明为乾知、乾元。当然,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因为乾对坤有首出性和先导性。这两处都提到“混沌”,说明未有天地万物时就有此灵明,因此灵明是天地之根、万有之基,不生不灭,有着亘万古而常新之永恒性,推动万有生生不息。
王畿提出的“一念灵明”凸显了良知呈现的当下性。林月惠认为,王畿所论良知作为“一念灵明”,“亦即是良知本体的发用,其根源性实践动力是当下具足,沛然莫之能御”(林月惠,第20页)。王畿说:“阳明先师提出良知两字,乃生身受命之灵窍,其机之在一念入微,使知有用力之地。譬之赤日丽空,而魑魅魍魉,自无所遁其形也。”(《王畿集》,第415页)另外,他还评论裘鲁江,说其“三十年来,未尝转念,遇有意欲未化,只在一念上照察,煅炼销融,以求复此灵明之体,固不从世情嗜欲上放出路,亦不向玄妙见解上借入头,可谓卓然独立不惧者矣”(同上,第456页)。在一念之微上察照,照破世情嗜欲,卓然独立以恢复灵明之体,这是王畿良知工夫论的重要特色。王畿所说“一念”同时包含着自反、逆觉的特征:“灵知在人,本然完具,一念自反,即悟本心,无待于修。”(《王畿集》,第581页)彭国翔认为,“龙溪在晚年所格外强调的一念工夫,实际上是先天正心之学与后天诚意之学的统一”(彭国翔,第145页)。王畿还说:“今心为念,是为见在心,所谓正念也:二心为念,是为将迎心,所谓邪念也。”(《王畿集》,第501—502页)因此,“一念灵明”之“一念”可谓“即正念,即本心”(吴震,2016年,第482页),是良知本体。同时,“一念”所证、所契入之灵明又直通天地之本源。
需要指出的是,王畿重视“一念之微”之当下动心起念,这可能受到慧能强调当下“一念”重要性的影响。正如慧能所说“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坛经·般若品》),“一念悟时,众生是佛”(同上),“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同上),“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同上),“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坛经·定慧品》),“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知见。佛,犹觉也”(《坛经·机缘品》)。王畿的“一念”工夫与慧能“善自护念”的禅法有相近处。他甚至还说,“一念者无念也,即念而离念也。故君子之学,以无念为宗”(《王畿集》,第440页)。
“一念灵明”即是良知,“良知灵明,原是无物不照,以其变化不可捉摸,故亦易于随物”(同上,第456页),故而需要不昧、不欺等格物诚意的工夫来恢复灵明本体。同时,王畿主张“一念灵明无内外、无方所,戒惧恐惧亦无内外、无方所。识得本体原是变动不居,不可以为典要,虽终日变化云为,莫非本体之周流”(同上,第683页)。因此,不能喜静厌动,而要在事上磨练。虽然如此,王畿还是非常重视静中涵养的工夫:“涵养工夫贵在精专接续,如鸡抱卵,先正尝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点真阳种子方抱得成,若是无阳之卵,抱之虽勤,终成假卵。学者须识得真种子,方不枉费工夫。明道云‘学者须先识仁’,吾人心中一点灵明便是真种子,原是生生不息之机。种子全在卵上,全体精神只是保护得,非能以其精神助益之也。”(同上,第98—99页)对此,陈立胜指出,“‘如鸡抱卵’,语出养生家,朱子曾用于描述涵养工夫,‘先正尝有是言’,当指朱子。显然在王龙溪看来,朱子之涵养乃是无真阳种子之空头的涵养”(王正主编,第171页)。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龙溪这里的“真种子”之说,显然与上文李道纯强调“真种子”只能是至纯无杂的灵明的观点非常相似。当然,相对而言,王畿这里特别强调此灵明是“生生之机”,以灵明为生生之根源和动力。
王畿也常用“一点灵明”一词:“念中有得有失,此一点灵明,不为念转;境上有逆有顺,此一点灵明,不为境夺;人情有向有背,此一点灵明,不为情迁。缘此一点灵明,穷天穷地,穷四海,穷万古,本无加损,本无得丧,是自己性命之根。”(《王畿集》,第91—92页)此“一点灵明”,类似佛教所说不生不灭、如如不动的真如空灵之性。王畿强调灵明的主宰性,提出“此一点灵明做得主,方是归根真消息”(同上,第92页),“吾人从生至死,只有此一点灵明本心,为之主宰”(同上,第160页)。在他看来,灵明不但有主宰性,而且不生不灭,是永恒的光明:“今日良知之学原是范围三教宗盟,一点灵明充塞宇宙,羲皇、尧舜、文王、孔子诸圣人皆不能外此别有建立。灵性在宇宙间,万古一日,本无生死,亦无大小。”(同上,第762页)此处“无生死”“无大小”,都表示灵明超越经验时空。王畿以良知学范围贯通三教,其所论良知既类似佛性真如,也类似道教所说“不坏元神”。他说,“大抵我师良知两字,万劫不坏之元神,范围三教大总持”(同上,第202页),“良知虚寂明通,是无始以来不坏元神,本无生,本无死”(同上,第777页)。
比较特别的是,王畿还持知气统一说。他认为,“千古圣贤只一知字尽之,知是贯彻天地万物之灵气”(同上,第704页),“通天地万物一气耳,良知,气之灵。生天生地生万物,而灵气无乎不贯,是谓生生之易。此千圣之学脉也”(同上,第348页)。此灵气也可以是一种神气,生化万物并推动万物生生不息。阳明虽然没有用到“灵气”一词,但阳明所说“精灵”大概也就是王畿所说“灵气”,或者说王畿之灵气说发挥了阳明之精灵说。“精灵”“灵气”“灵明”皆有生天生地之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比较好理解良知的本体论乃至宇宙论意义。良知是“灵明”“精灵”“灵气”,超出了狭义的主体知性范畴意义。良知是天地灵气的显现,能贯通万物为一体。王畿还说,“天地之灵气结而为心,心之灵明谓之知”(同上,第386页)。蒙培元认为,“王阳明所说的‘灵明’,仍然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王畿从这里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他以‘灵气’为良知,这良知就是形而下者,这样,良知就变成了心的生理、心理特征,已不具有形而上的性质了”(蒙培元,第56页)。在王畿这里,我们不能因为他说良知是灵气,就认为其良知是形而下的,其所说灵气实际上相当于“道”,仍然具有形而上之特征。关于灵气的形而上意义,《管子·内业》篇早有揭示:“灵气在心,一来一逝。其细无内,其大无外,所以失之,以躁为害,心能执静,道将自定。”心能静定,灵气自然来归、呈现,此灵气就是形而上之“道”。
王畿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神与气而已矣。神为气之主宰,气为神之流行。神为性,气为命。良知者,神气之奥,性命之灵枢也。良知致,则神气交而性命全,其机不外乎一念之微”(《王畿集》,第508页)。又说良知“其机不出于一念之微。良知之主宰,即所谓神;良知之流行,即所谓气”(同上,第419页)。从这里来看,王畿把阳明的良知说与身心性命、生命机能密切结合起来,这与阳明以良知为精、气、神统一体的思想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他们均以气为良知之流行,但阳明以神为良知之妙用,王畿以神为良知之主宰。可以说,在王畿那里,良知是神气合一的灵明状态。
王畿还说:“良知先天而不违,天即良知也;良知后天而奉时,良知即天也。故曰:‘知之一字,众妙之门。’”(同上,第419页)由此可见,王畿受到宗密一系佛学思想的影响。他又说:“虚寂原是良知之体,明觉原是良知之用,体用一原,原无先后之分。”(同上,第694页)这与宗密所论“寂而知”的思想十分相似。刘宗周曾批评说,“至龙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悬空期个悟,终成玩弄光景”(《明儒学案·师说》)。若就王畿的思想与禅学的相似处而言,这有一定道理。但王畿对气与生生的强调,甚至以良知为灵气,这显然又与禅学迥别。因此,我们不能把王畿简单地归于禅学。当然,禅学与儒学也并非不可相互借鉴,实际上,慧能的思想也融入了一定的儒学因素。
四 余论
良知灵明与气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也关联到性理与气的关系。阳明门人后学对此有不少讨论,而且意见不一。有的视气为根本,如南中王门唐鹤征说“人以为斯理斯道斯性斯命,极天下之至灵,非气之所能为,不知舍气则无有此灵矣”(《明儒学案》卷二十六),又说“盈天地只有一气。其所谓理,所谓性,所谓神,总之是此气之最清处。清便虚,便明,便灵,便觉,只是养得气清,虚明灵觉种种皆具矣”(同上)。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论断也代表了晚明时期为对治理一元论的流弊而侧重气一元论的发展趋向。然而,唐鹤征此论并不符合阳明学的精神。如果将灵明归于气之清,则良知灵明的本体性、本源性就无从谈起,这就陷入程颢批评张载“清极则神”之境地:“气外无神,神外无气。或者谓清者神,则浊者非神乎?”(《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
泰州学派徐樾说:“运动者曰气,虚灵者曰神,皆拟而名之者也。不神则无物矣,谁其运动?”(《明儒学案》卷三十二)这是说“神”“气”是对同一个存在的不同称谓。在他看来,“神”更具有根本性。阳明弟子聂豹论及灵明与气的关系时,也特别强调灵明对气的超越性和根本性。他说:“灵明乘气机,迭运不息,通乎昼夜之道,无分于寂感。”(《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十)“何以生人?此灵明;生物,亦此灵明,与上古不异。”(同上)显然,生人生物的灵明是先天的宇宙本体,是永恒的。同时,灵明乘气机而行,就人而言,“气有盛衰,而灵无老少”(《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十)。聂豹在《答陈明水》中说:“心是生身之始,犹始祖也。灵明合气以成形。有心而后有身,而后有知,有意,而意之所及,则物也。”(《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十一)作为“生身之始”的心也是就先天的宇宙灵明而言,聂豹这里与邵雍所说“心在天地前,身在天地后”(《伊川击壤集》卷十九)之心相近,此心非身体官能之心脏,也不限于后天的大脑意识活动。
若按唐鹤征的理解,“清便虚,便明,便灵,便觉”,实际上有以“形气之灵识为知”的危险。对此,阳明再传弟子王时槐(号塘南)一针见血地指出,“夫知者,先天之发窍也。谓之发窍,则已属后天矣。虽属后天,而形气不足以干之。故‘知’之一字,内不倚于空寂,外不堕于形气,此孔门之所谓中也。末世学者,往往以堕于形气之灵识为知,此圣学之所以滋晦也”(《王时槐集》,第344页)。就是说,对于良知,我们不能从后天经验“有身而后有心”的角度来理解,而是要从先天而后天、后天而先天统合的角度来理解,即良知虽不离气,但其对气有超越性。程海霞认为,这段话代表了王时槐“儒门中道观在本体层面的提出”(程海霞,第16页),并主张“阳明以良知为本体的为学主旨,在其二传弟子王塘南那里得到了继承。但塘南对此‘知’的具体论述,在思路上已经完全不同于阳明”(同上,第16页)。此论未必十分恰当,但王时槐明确否定以灵明论良知,这确实是其与阳明在良知问题上的一个重要区别。大概是鉴于时人有把“一点灵明”理解为识神的误解,王时槐否定以灵明论良知:“夫本性真觉,原无灵明一点之相,此性遍满十方,贯彻古今。盖觉本无觉,是谓无生,既云无生,安有死乎?”(《王时槐集》,第438页)“若有一点灵明不化,即是识神。”(同上,第438页)“识神既不用事,则浑然先天境界,非思议所及也。果能悟此,则形骸本非有无,沉痾自脱然矣。即今果能大休歇,一丝不挂,复归混沌之初,亦无天地万物,亦无世界,亦无形骸,亦无古今,其庶几乎!”(同上,第438页)其实,“本性真觉”就是灵明之本义,即是无天地万物、无世界、无形骸、无古今之混沌之初。
总体来说,与神气关系类似,灵明与气的关系问题,在阳明学中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强调灵明是一种灵气或气之灵,有的则坚决反对将灵明与气二者混同。以阳明强调“一也”之圆融整体思维来看,灵明与气是一体不可分的,或者说类似老子所说“此两者同出而异名”(《老子·第一章》),不同的名相只是对同一存在之不同层面及其功能的称谓。但是,既然用异名作出区分,那两者就有所区别。相对而言,气容易被对象化,是意象性存在,在理学话语中,更多被界定为形而下存在,这是有其道理的;而灵明贯通本体、主体为一,只有超越或泯灭对象性、意象性,才能进入由“混沌”而显现灵明神妙之境。同时,与理气关系、性气关系类似,朱子反复强调“理”的先在性与优先性,阳明则强调性对气有主宰性。那么,良知作为天理、天命之性的灵明状态,虽然不离气,但对气又有超越和主宰性。泰州学派方学渐说,“流行者气也,主宰者理也”,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我们对气与灵明关系的理解,即灵明为主宰、气为流行。对此,吴震也强调,“作为‘我的灵明’的良知不就是气,气构成宇宙万物的要素条件,它充满宇宙,但气不能决定良知的存在,否则便近乎理为气所决定的气本论。在阳明,良知才是气乃至于万物之中的本体存在”(吴震,2011年,第138页)。陈立胜认为,“就其作为造化的精灵的论述看,良知诚是一生生的功能性,其‘功能性’具体表现于其感通与感应的能力······就其作为致良知工夫论述看,良知则又是一知善知恶的知体,而致良知则不过由此知善知恶的‘知’入手,知其善则善之,知其恶则恶,在此意义上良知的确又是一意识现象······‘生生的功能性’乃是天理、仁理、性理,而天理、仁理、性理之‘灵明’‘明觉’方是‘良知’”(陈立胜,第120页)。此论对阳明良知思想的揭示也颇为深刻全面。就生生的功能性而言,良知离不开气。良知主要是指其生理之灵明、明觉,此种灵觉虽由气而显,但不可简单归于气,而要看到其对气的超越性、主宰性。此良知灵明与先秦儒家所说“帝心”“天心”“天地之心”的说法可谓是相通的。
注释
*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易传》与宋明理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编号22BZX051)的阶段性成果。
[1]《答聂文蔚书》也提到,“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1册,第86页)。就此而言,阳明与学生的这段问答也当在1526年或阳明去世前的两年。
[2]朱承认为,“合一性是王阳明哲学思维最为突出的特质之一。无论是在对于世界本质的总体把握上,还是在对认知与行动、不同修养工夫、人与天地万物等之间关系的理解上,王阳明哲学都呈现出了合一性的思维特质”(朱承,第66页)。
[3]张学智认为,“王阳明的良知是‘大’良知,大良知是在道德意识基础上精神活动的种种构成因素的协调、整合。大良知是‘精神’或说‘心体’的代名词。它由道德意识、理性、意志、情感、直觉等精神活动的因素构成”(张学智,第74页)。全面来看,宇宙论层面的良知精灵说乃真正的“大良知”。
参考文献
古籍:《葆光集》《禅门师资承袭图》《禅源诸诠集都序》《重阳全真集》《传习录》《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道院集要》《法藏碎金录》《管子》《河南程氏粹言》《河南程氏遗书》《华严经行愿品疏钞》《黄氏日抄》《景德传灯录》《老子》《乐邦文类》《礼记》《隆兴佛教编年通论》《陆九渊集》《论语》《蒙斋集》《蒙斋中庸讲义》《明儒学案》《蒲室集》《邵雍集》《双江聂先生文集》《水云集》《坛经》《无异元来禅师广录》《勿轩集》《仙乐集》《心学宗》《玄教大公案》《伊川击壤集》《圆觉经》《圆觉经大疏钞》《圆觉经略疏钞》《圆觉经略疏注》《远真集》《昭德新编》《肇论新疏》《中和集》《周易》《庄子》等。
陈来 2019年:《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载《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第2期。
2020年:《王阳明晚年思想的感应论》,载《深圳社会科学》第2期。
陈立胜 2018年:《良知之为“造化的精灵”:王阳明思想中的气的面向》,载《社会科学》第8期。
程海霞 2017年:《中晚明思想家王塘南“儒门中道观”详释》,载《浙江学刊》第3期。
邓晓芒 2020年:《黑格尔哲学讲演录》,商务印书馆。
《方立天讲谈录》 2014年,九州出版社。
贺麟 2019年:《黑格尔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林月惠 2014年:《阳明与阳明后学的“良知”概念——从耿宁〈论王阳明“良知”概念的演变及其双义性〉谈起》,载《哲学分析》第4期。
蒙培元 1986年:《从王畿看良知说的演变》,载《哲学研究》第10期。
彭国翔 2005年:《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王畿集》,2007年,吴震编校整理,凤凰出版社。
《王时槐集》,2015年,钱明、程海霞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阳明全集(新编本)》,2010年,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浙江古籍出版社。
王正主编,2018年:《儒家工夫论》,华文出版社。
吴震,2011年:《〈传习录〉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年:《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徐爱 钱德洪 董沄集》,2007年,钱明编校整理,凤凰出版社。
《杨简全集》,2015年,董平校点,浙江大学出版社。
张学智,2018年:《牟宗三“良知坎陷说”新议》,载《国学学刊》第1期。
朱承,2023年:《王阳明的合一性思维及其旨趣》,载《哲学研究》第10期。
《朱子全书》,2010年,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邹守益集》,2007年,董平编校整理,凤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