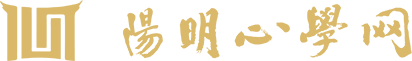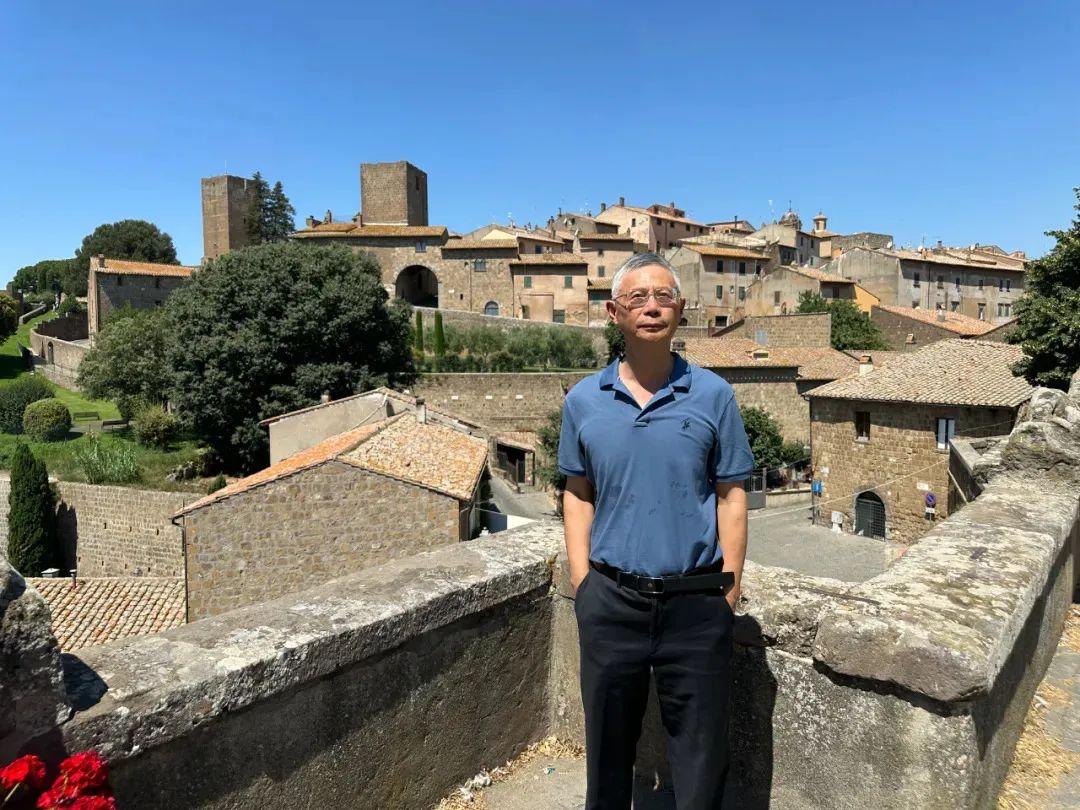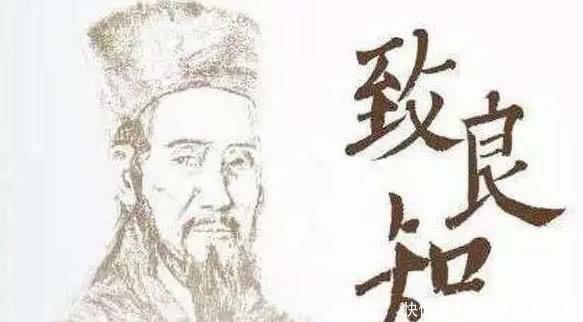顾久,教授,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原馆长,《贵州文库》总纂,研究方向为语言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
基金项目:贵州省201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贵州自然环境演变与人文发展关系史研究”(17GZWH02)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阳明文化要转化运用于当今社会,需要“由古而今,由士而民,由书而实”,需要与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话语衔接并融合,更需要理论的创新。研究提出并阐释“生物—生态—生态哲学”的三维生态新理论视角,分析王阳明的个体生物学禀赋,以及他处身的明代中期的“明清小冰期”自然生态,面对由此引发、衍生的外寇入侵,明军避遁与募兵,白银货币化,帝制农商社会等局面,他遭遇了谋生方式、组织秩序、行为秩序、心态秩序等明朝社会全面危机。王阳明处此时代,对当时的人文生态进行反思批判,对朝廷官场采取疏离立场;为安身立命,他不断追寻并创新中华学脉,最终能代表时代,提出并阐发了自己的“心学”理论。
关键词:“生物—生态—生态哲学”;三维生态观;阳明心学;阳明文化转化运用
“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是中共贵州省委提出并重点实施的“四大文化工程”之一。“阳明文化”含义广泛,本研究关注的是对王阳明其人其学的内容宣介、学理阐发、价值评价、精神传承等形成的社会环境因素。而“转化运用”中的“转化”,应是由古代思想转化为当今思想,由学者话语转化为百姓常识,由书本知识转化为社会实践,即“由古而今,由士而民,由书而实”。此外,当“转化”与“运用”联用时,是理论与实践的并举;分言时,“转化”应重在阳明心学向现代话语转换的理论思考,而“运用”重在阳明文化在现实社会的实践举措。
本文关注“转化”,即阳明心学向现代话语的理论转换,提出“生物—生态—生态哲学”的三维新理论框架,分析阳明心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研究拟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阳明心学进行转换的理论思考,二是用新的框架阐释阳明文化的发生。分述如下。
一、对阳明心学进行转换的理论思考
(一)阳明文化的现状
时下阳明文化传播阐发蔚然成风,细审其构成,主要有主流意识形态、专家学者和社会群体这三种视角与话语。“主流意识形态”,指主流媒体等正面肯定王阳明及其心学,大量引用其语句而形成的主导性话语;“专家学者”,指有关研究专家的学术话语;“社会群体”,指以企业家为主体的社会群体研习阳明文化的话语。
三种话语各有其产生的缘由和背景,或因中国进入世俗的市场经济时期,主流媒体倡导弘扬阳明心学及中华传统文化,意在纠正长期以来的西化弊端,再塑国民信仰,振奋民众和干部的精气神,激扬心力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倡导弘扬阳明心学及中华传统文化指令性强,学理性弱,既难以与马克思主义话语完美契合,又难以与眼下市场社会群体无意识相融。学者(主要是哲学、思想史领域)话语,重在研讨阳明心学的学术机理,意欲以此教化民众,提升中国人的精神境界。但重理性,轻情绪;重精英,轻百姓;重理论,轻集体无意识;重应然,轻实然。影响一般知识阶层尚难,说服社会大众更不易。社会话语的主体是企业家群体,该群体需要强大心力以坚守良知、精进管理、拼搏商海、勇于创新等,但其学理欠深,常带“成功学”的实用色彩,还难免产生跟风、重复的庸俗风气。
上述视角多元并存,具有历史合理性及存在必要性,也部分欠缺对阳明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当代现实生活的理性考察。于是,怎样使阳明文化既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又具备学理,还能够深入民众心灵,还需要突破障碍,进一步创新理论。
(二)阳明文化走进当代的理论障碍
要将阳明文化转化为当代话语,主要有两个障碍:一是改革开放之前僵化的学术思想;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话语。
前者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史》(1957年版),以阶级斗争学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为依据,对王阳明的政治立场与思想方法进行了批判:政治方面,认为王阳明立足地主阶级立场,其事功主要是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思想方面,则主要批判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据此,认定阳明心学是没落、反动而毫无价值的。该书还认为,王阳明的事功“其本质就是对农民群众采取军事的、政治的以及思想上的高压统治政策”[1]880。另外,王阳明的理论“近则接踵陆象山、陈献章,远则继承了曾子—子思—孟子的主观唯心主义传统”[1]883。
“科学”话语方面,《中国思想通史》(1957年版)在举“南镇花树”之例批判王阳明时,援引列宁“一定长度和一定速度的光波运动,它们作用在眼网膜上,就在人里面引起这种或那种颜色的感觉”的自然科学结论[1]884。此前,晚清协和书院院长谢卫楼也尖锐批评含王阳明心学在内的儒家学说“与科学知识对立”的“反科学倾向”①(谢卫楼认为,王阳明心学在内的儒学“有六大问题,第一膜拜先祖,缺乏自由观念;第二是用理气性命解释一切,呈现非知识倾向;第三是试图对天地追究终极道理,并把‘天道天理’推至虚幻,而与科学知识对立;第四是尽管历史证明人性恶,但儒家却总说人性善,所以,不能以制度和法律来建立秩序;第五是儒家崇拜圣贤,对于一切学问,都以圣人言论裁度,不能坚持人的理性;第六是儒家对于自然用理气相感来解释,有反科学倾向”。见葛兆光,《到后台看历史卸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19.)。这反映了近代以来科学主义的立场已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科学主义几乎成为“正确”“权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义词。
因此,阳明心学的转化与传播,不能不注重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话语的对接与融合。
(三)一种新的理论思考
综合已经比较成熟的自然科学成果,如生物学、生态学、生态哲学等,并以其相互递进的理论视角,可以形成“生物—生态—生态哲学”三维生态观的框架,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能与当代自然科学相结合,从而拓宽视野、创新理论。
该理性框架有三个基点。
第一,“人是生物”。根据常识,即使是杰出人物,包括王阳明及所有的圣贤帝王,都不过是人类这个生物物种中的一员②(人类不过是原子、由此构成的复杂分子、细胞、组织器官等的集成体;人类基因与青草的基因相似度约17%,与老鼠的约80%,与黑猩猩的接近98%;而各民族、肤色人种之间的差异,只有大约0.05%。见陈守良、葛明德编著,《人类生物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所以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2]209,恩格斯也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3]当然,从原子到基因,从青草到人类,自然演化的每个“突显”(Emergence)都是量变后的质变,不能再返回简单要素来分析:“在一个结构系统下整合出较高层级的过程中,会突显一些全新的特质,而且这些新特质是无法从低层组成的特性中预测得知的。”[4]人类演化到能用自身智慧来反思自身行为,寻求向死而生的意义与超越,考虑自身与万物的关系等等,就已经处于所有生物的最高生态位。
“人是生物”还可推导出应以生物学视野看世界。人类看世界的视角,早先有宗教(或准宗教)世界观。阳明心学以及中国传统学术自来带有准宗教的意蕴,中国传统学问重心灵、重人生、重道德,重直觉、重妙悟,重践履,而非西学的重外界、重客观、重理性、重试验、重发现、重思辨。因此“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成分(儒、道、释)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宗教性思维方式”[5]10,“良知或心体……无论就其强调功夫,还是强调顿悟,王阳明的本体均接近于宗教义本体”[5]80。近代以来,西方自然科学主要以物理学观照世界。当代,有学者倡导新的生物学世界观。物理学的与生物学的区别是:前者是化约的、简单的、线性的,带有决定论的倾向;而后者是系统的、复杂的、偶然的、特色的、多层的,带有或然性的学理[6]。显然,生物学的世界观,更符合现实世界的实际,也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第二,“生态”。人类既然属生物中的一类,就需要生态系统来支撑其生存。“通俗地理解,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重点考量生物与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实,从物种进化与生存的角度来看,生物都是有智慧的,每一种生物都是在适应自然环境中不断进化的。因此,从这层意义上来看,生态学是研究生物生存智慧的科学”[7]。此外,不仅人类与外部的自然世界形成生态关系,其身体内部本身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生态系统:“在我们体内和体表的10000个菌种平均各有2000~4000个基因。这意味着,在人体内和体表约有2000万个细菌基因在活动,并且此刻在体内被转录和翻译为蛋白质的各色基因中仅有约0.1%属于人类自身。”[8]这些要素形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外部条件——自然生态。当然,人类作为生态位中高端物种,其生存除了需要与自然生态进行错综复杂的积极互动外,还必然会在生存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系统的内部机制——人文生态。因此,我们将生态区分为两大类:“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
这里的自然生态,指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如地形地貌,气候气象,土地土壤,物产资源等要素;人文生态,指人群得以存活的人文要素,如谋生方式,组织秩序,行为秩序,心态秩序等要素。两种生态及其间各要素有机相关。比如对应着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中国大地上有一条年降雨量400毫米的隐形界线,即所谓“胡惟庸线”。因降雨影响的地形地貌,相应土壤条件,以及物产资源,“胡惟庸线”将游牧与农耕文明划分开来——400毫米降雨是种植业、农业生产的底线。自然生态带来两种不同的谋生方式,由此产生不同组织方式、日常习俗和不一样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两种生态,下文将结合阳明心学的发生进一步说明。
第三,“生态哲学”。由于生存要素错综繁杂,就会启迪人们用新的视角去思考把握人生与世界,“生态”便也迅速扩展至生活各领域,最终形成认识、思考外界的理论框架和实践的方法论,即“生态哲学”。其实,恩格斯早就说过:“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9]在这个“无穷无尽”的画面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都成为统一有机的生态体。“当代美国物理学家F.卡普拉认为,生态哲学是现代科学世界观,是科学最前沿的人的观点。他说:‘一种新生态世界观正在形成,其科学形式是由系统理论赋予的’。他把生态哲学理解为生态世界观,是转变以往价值观而形成的新的生态世界观。”[10]显然,这个“生物—生态—生态哲学”的三维视角,与传统宗教学、物理学、政治学等视野,有显著的差别:除人类的思想观念之外,还关注自然气候及资源;除理性外,还关注直觉情绪与潜意识;除精英的、文本的思想史内容外,还关注百姓的群体无意识及社会生活场景;除顾及思想的相对独立与传承外,还关注思想者的生物个体差异性;除意识形态、思想、企业等视角外,还包含了更多的复杂学科。因此“生物—生态—生态哲学”的三维理论具有比传统理论更多的复杂性与系统性、多层级性、偶然性、耦合性等,摒弃了传统布道、信奉、追随的宗教学思维方式,摒弃了传统化约、线性、简单因果等物理学的思维方式。既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也符合当代科学的结论。
从生态哲学的角度,对阳明思想产生和基本特点的考察,不仅是考虑单纯的学理层面的思想脉络,更结合生物人的特征、生态的系统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生态哲学,即系统化的思想产生理论。从生态哲学的角度来进行阳明思想的阐释,不是一种单一的、线性的呈现,而是一种多线条的、系统的、相互影响的复合生态体系,从这样一个角度,可以更为宏观、多层面、耦合地呈现阳明心学思想的发生与特点。
从这个新的理论视野出发,才能更好认识阳明文化与当代文化,完成“由古而今,由士而民,由书而实”的理论转化。
二、以新框架阐释阳明文化的发生
在“生物—生态—生态哲学”三维框架下,审视王阳明及其心学,不再采用宗教(准宗教)、物理学视角,将其人视为天纵英才,将心学视为神圣的秘谕,或将王阳明及其心学视为简单化、实用化、概念化的存在,而是把王阳明视为一个活生生的生物人,考察其在特定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下的思考、行动与宣言。下面,从作为生物个体的王阳明,其处身时段的自然生态,其特定的人文生态,心学的基本特征等四方面进行分析。
(一)作为生物个体的王阳明
王阳明只是一个寻常的生物人类个体,而所有人类个体都是由先天与后天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从先天方面来看,人类遗传基因对孩子未来的形貌、特长、个性、气质等有相当大的影响。研究发现,“人类的心智指标,从智商到记忆力,从幸福感到自信心,甚至是政治倾向和宗教信仰,遗传都是最大的影响因素。而且世界各地的研究者都得到了差不多同样的结果:在绝大多数指标中,遗传的贡献率都在50%~70%。也就是说,从受精卵形成、生命孕育的那一刻开始,遗传物质就已经为我们每个人的心智准备了一张蓝图”[11]227,229。王阳明所展现的聪敏好学、心高自尊、执着自信、大胆灵活等独特个性特征,用陈来先生的话来说,有“豪雄”秉性。“王阳明的个人气质在一个方面近于古人所谓‘豪雄’,他的学生都认为他属于‘才雄’‘雄杰’‘命世人豪’。历史记载一致说他少年即‘豪迈不羁’,他少时逃学,常率同伴做军事游戏……正是由于他从不循规蹈矩、拘泥末节,青年时任侠骑射,留情兵武……在平南赣及平藩后险恶的政治危机中展示的惊人的军事谋略和高度的政治技巧、由此取得的功业,乃至由此对现代政治家产生的魅力,都须以‘豪雄’这一面为基础才能彻底了解”[12]。
从后天方面来说,人的心智形成还有赖于其生长的环境、经历、学习、修养等要素,共同来构建特定的神经元“连接组”。此中,大脑神经元会不断“重新赋权,重新连接,重新连线,重新生成……与此同时,这四个‘重新’也受基因的指挥。基因确实会影响心智,尤其是在幼年和童年,大脑开始建立连接的时候”[13]。王阳明早期的家族背景,此后的受教育过程,成年曲折磨砺的经历,晚年的反思与总结等等,都会不断重组其大脑“连接组”。
因此,王阳明的心智架构,如聪敏向学、心高自尊等,应主要由其先天的独特基因造就;而担当责任、愈挫愈勇、恪守良知等素质,更多应该由其后天的家学、入宦、受挫、坚守等境遇与历练有关。
(二)从自然生态看阳明心学的产生
我们认为,对传统农耕社会最有影响的自然生态,可从气候气象、地形地貌、土地土壤、物产资源等要素考察。自然生态不直接作用于思想,但通过影响人类的谋生方式,引发组织、习俗等秩序的变迁而作用于人的心态。
在王阳明生活的1472到1529年间,正处于“明清小冰期”较为严重的时期——1476年,太湖结冰;1493年,苏北沿海结冰;1509年,黄浦江结冰,且“厚二三尺,经月不解,骑马负担者行冰上如平地”;1512年,洞庭湖结冰,最深处达一尺。另有记载说,1515年河北文安的冰柱竟高达5丈……[14]等等,气候变化直接导致农产品的减产,“一般而言,在北半球,年平均气温每增减1摄氏度,会使农作物的生长期增减3—4周……据张家诚的研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温度变化1摄氏度,粮食亩产量相应变化为10%”[15]。农产品减产又引发国内的饥荒。自王阳明出生,常有因灾食人的事件记载,饥荒导致国内动乱,如正德七年(1512)王阳明在《上父亲大人》所言:“近甸及山东盗贼奔突往来不常,河南新失大将,贼势愈张”[16]1787,这里应指当时刘六、刘七的农民大起义。而王阳明后来平息民乱,也与小冰期导致的自然灾害相关。
更严重的是,北方游牧者因气候酷寒,草畜死亡,不断发动南侵。早在弘治年间,蒙古部落已在河套一带形成“套寇”,在河套地区杀掠男女、焚毁屋庐、抢掠马牛。至正德年间,河套边患愈演愈烈,以致武宗皇帝御驾亲征,在应州附近与蒙古军队激战。同时,由于小冰期导致草原贫瘠,造成大量游牧民涌入明朝的同时,也加剧了袭击的发生[17]。这些边患,是青少年王阳明修习兵书,胸怀经略天下之志的客观社会背景。
为防止入侵,明朝设立了辽东、蓟州等九个边防重镇。兵源先用父子相承、戍防一体的“世兵制”,但随着小冰期的降临和长期开发导致的土地退化,耕作日益困难,“尤其在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灾害几乎年年发生……连年灾祸军民乏食,不少士兵选择逃亡,土地大量抛荒”[18]。
外寇入侵,军户逃逸,迫使明代军制不得不迅速从“世兵制”变革为雇佣兵的“募兵制”。雇佣报酬,先是免税赋、发津贴,迅速过渡到直接发放白银,到了弘治年间的募兵,所给的待遇为“人给银五两”,相较于前,银饷提高了五倍。国防经费是明廷的一笔硬性大支出,白银募兵直接推进了明代中期的白银货币化,募兵制与白银货币化两项重大改革的正式进程,恰好都发生于明英宗正统年间。
总之,明代中期的小冰期发生,像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块,引发了社会机制和体制的全面危机与变革。
(三)从人文生态看阳明心学的产生
我们首先基于人是生物——需要谋生;同时人还是一种社会化生物——需要共同的组织、行为与心态秩序,才能维系生存。于是,“人文生态”从谋生方式,组织秩序,行为秩序与心态秩序等四方面逐项分析。
1.谋生方式
白银货币化,促使了明中期整个社会从传统农耕“实物经济”向帝制农商的“货币经济”迅速转化,引发了全社会的大变革大震动[19]。这是王阳明及其心学极重要的社会经济背景。
一方面,据黄仁宇统计,至1600年,明朝源于农业土地的总收入为“2500万两,甚至接近于3000万两白银”[20]246-247;而从1570到1590年的工商业收入,即便加上“国家管理收入”“役和土贡折色”等,三者总计也才378万两白银[20]371。可见明中期仍然以农耕为主要谋生手段。
但另一方面,自正统“弛用银禁”,至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全社会出现白银货币化:“大量事实说明,明朝成、弘以后,白银货币化自上而下全面铺开,带来社会经济货币化的急速发展……与社会诸因素变化相互作用,根本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和面貌。”[21]白银货币化全面引发传统制度的解体,“考诸历史事实可以发现,明朝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几乎无一例外地均与白银相关,也就是说白银货币化不仅波及国计民生方方面面,而且直接或间接引发了明朝一系列制度的崩坏:黄册制度破坏,户籍管理制度衰亡;乡村基层组织里甲性质发生变化……乡村社会分化加剧;军屯、商屯、民屯破坏;工匠制崩坏;开中制瓦解……几乎所有明初制度都连带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崩坏和演变”[22]。
由传统农业向白银货币化为标志的帝制农商这种根本谋生方式的转化与冲击,全面深刻地颠覆了传统的组织秩序、行为秩序和心态秩序。
2.组织秩序
在这方面,王阳明时期的朝廷重要领导者们显得既失范,又失能。
中国传统组织秩序源于农耕社会基础上的家长制。该格局犹如大家庭,这种组织秩序中的皇帝,明显带有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型”特征,需要“君父”和“家长们”的权威和榜样的魅力来维系。但作为君父的明武宗,以刘瑾为代表的“家长们”显然失去了模范意义——“失范”。
从生物学的角度审视武宗皇帝与巨宦刘瑾,前者明显带有“青春期叛逆”的表现,而后者分明具有出身寒微追求“过度补偿心理”的倾向。正德皇帝的叛逆表现在放纵肉体,建豹房,宠幸优伶;偏爱经商赚钱,最荒唐者,他亲自站柜台经商,“尝亲扮商贾,与六店贸易,争忿喧诟。既罢,就宿廊下”。刘瑾则显示出宦官的贪婪:1522至1532年,太仓库平均每年的白银收入是200万两,而刘瑾被抄家时,搜出的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贪腐到“富可敌国”[23]。
失能,指统治者把控社会的能力,这里主要讲对金融管理的失控。“明朝政府失去通过货币发行调控市场的能力和利用货币流通量控制增加财政弹性的能力,却又大幅度地转入要求政府功能更为强化的货币财政体制,所以明朝在白银货币化开始的时候,其实就开始一步步走向财政困境……只能采取公开增加赋税甚至公开掠夺的方式满足财政需求和皇室开支,从而直接激化了统治阶层与社会的矛盾……成为加剧全面社会危机的基本因素。”[24]这段论述指明了明朝政府失能的关键原因是对货币金融管理的失控。总体看,明朝无专门的金融人才,无有效的管理机制,在帝制的农商架构中,管理者最关心的是从生产者处收取足够财税,以提供自身利益(宫廷开支、宗室俸禄等)和政权稳固与运转(官僚俸禄、军队开支等)。从货币的使用与管理看,可以说无发行数量的论证,无市场的供需分析,更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25]492。明朝中期以前,法定的货币是宝钞与铜钱,但前者因出钞过多、收敛乏术而贬值,自弘治年间基本废弃不用[25]493,铜钱又因矿源不丰,邻国收紧,滥铸私钱等而影响贸易。自白银货币化以后,一方面,大量的白银来自海外,属走私,无记录难统计③(据估算,16到17世纪中叶,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美洲的大约3万吨,日本的8千吨,见樊树志,《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2024年,第197-199页。);另一方面,作为贵重金属的白银被官僚、商贾和市民竞相藏于户而埋于地,更是一笔糊涂账。
3.行为秩序
这里的“行为秩序”,主要指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习惯,或称“习俗”“风俗”等,含衣食住行、岁时年节、人生礼俗、民间俗信等。日常行为往往体现出共同体长期仪式化的行为秩序,能涵育人于无形之中。但明中期,全社会的行为秩序显得失节又失度。
失节,指失去农耕经济的节制而日益奢靡。略早于王阳明的王锜在《寓圃杂记》中记录下他眼中苏州城的变迁:正统、天顺间,所见“稍复其旧,然犹未盛”;至成化年间,每隔三四年上一趟城,“则见其迥若异境”;而至弘治时“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堪称“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26]。
失度,指失去传统的阶层等级而僭越礼秩。“至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迅猛,人们的消费欲望膨胀……突破礼制约束的行为时有发生。‘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房屋逾制之风兴盛,南京‘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浙江新昌县‘城中富官之家,多高堂广厦,杂用诸色木植,周围绕以砖墙,檐阿警革,丹艧相望’。服饰、房屋等僭越定制,突破了等级、身份的限制,冲击了封建礼制。”[27]“嘉靖《江阴县志》记载:‘国初时,民居尚俭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服布素……成化以后,富者之居,僭侔公室,丽裙丰膳,日以过求。’”[28]
4.心态秩序
白银货币化还导致传统心态的瓦解。马克思说:“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2]247在明朝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型的大背景下,货币化的白银,相比之前铜钞,价值更大,携带分割方便,更有利于储存,白银的这种新的货币形态,直接助推了明朝中晚期市场经济的极大繁荣,当社会的物质基础发生变化时,心态秩序的变化必然会出现。“货币原本是为人的交往活动服务的抽象符号,却反将人符号化,变人为微不足道的工具”[29]。于是,全社会从集体无意识到意识、到思想、到意识形态,多层面都显示出传统心态秩序的失衡与失序。
失衡,指传统农耕社会长期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失去了平衡。传统社会里,中国人以血缘纽带、熟人社会为根基,构成了历史悠久、强大稳固的心态秩序:在对大自然的关系上,崇尚天人合一;在对社会关系上,认同推己及人;在对自身利益和个性上,遵从克己复礼。但在白银货币化的冲击中,心态失去了平衡,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也迅速恶化。“按顾炎武的说法,明代社会风气的恶化始于成化年间。到正德时期,整个社会的道德堕落已经一发而不可收拾”。其中,“追求享受,崇尚奢华”“官僚贪污成风”“士人投靠权贵,朝臣结党营私,相互倾轧”“拜金主义盛行”这四条尤为显著[30]。
失序,指失去了传统意识形态的秩序。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人们大部分生活在血缘群体社会中,每个人都从属于群体。但这种秩序因为商业及货币的出现而变得个体与世俗化。在货币经济面前,“小农经济社会以及附着其上的社会结构、等级制度就像地震一样坍塌了;过去曾经认为神圣的、不能用货币衡量的伦理情感、价值观念逐渐消解了,生活世界中各种事物都货币化了”[31]。
总之,王阳明生活时期的人文生态是:从谋生方式看,在白银货币化潮流下,迅速从传统农耕社会向帝制农商社会转型;从组织秩序看,统治者明显“失范”与“失能”;从行为秩序看,普遍形成“失节”与“失度”;从心态秩序看,社会心态 “失衡”且“失序”。而这一切,共同构成了王阳明身处的时代的人文生态,深刻影响了其人其学。如果我们离开了上述特定的生态环境,会把王阳明及其心学的认识政治化、宗教化或经院学术化。
(四)生态哲学视野下的阳明心学基本特征
根据“生物—生态—生态哲学”的三维理论框架,定位阳明心学时,我们首先注重王阳明作为生物个体的禀赋,其次是该个体所处生态(自然与人文),最后是其思想特征。
据此分析,王阳明具有较独特的聪颖善学、心高气豪、自主自强的秉性;在其曲折奋发的人生道路上,他能对所处身时代的人文生态进行深切反思与批判,对朝廷官场采取相应疏离立场;另一方面,为了安顿灵魂,他不断追寻并创新中华学脉,最终代表时代,义无反顾、理直气壮地提出并阐发独到的“心学”理论。依次简述于下。
天性演进。王阳明自幼心高、自主、气豪,从幼时对父亲约束的反抗,青年时对军事家的向往与对科举的相对淡漠,成年后对时尚的“文章气节”及“乡愿”的不断反思与超越,终而达成“狂者”境界。关于“狂”,王阳明曾说:“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32]127从而获得个性上的大解脱大自由。
对时代的反思与批判。王阳明对那个时代是痛心与失望的。在《答储柴墟书》中哀叹:“今天下波颓风靡……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33]在《上父亲大人二札》中吐露:“朝廷费出日新月盛,养子、番僧、伶人、优妇居禁中以千数计,皆锦衣玉食……中间男亦有难言者,如哑子见鬼,不能为傍人道得,但自疑怖耳……祸变之兴,旦夕叵测……时事到此,亦是气数。……未知三四十年间,天下事又当何如也!”[16]1787-1788《与胡伯忠》又说:该时代“正人难得,正学难明,流俗难变,直道难容。”[34]晚年《答顾东桥书》还说:“呜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不亦拘滞而险艰乎?呜呼,可悲也已!”[35]62
对朝廷官场采取疏离态度。王阳明家族有隐逸传统,他一直有退隐的愿望,主要体现在请辞报告上。如《自劾乞休疏》,自称“叨位窃禄十有六年,中间鳏旷之罪多矣……正合摈废之列”,且“近年以来,疾病交攻,非独才之不堪,亦且力有不任”,请求“罢归田里,使得自附于乞休之末,臣之大幸”[36]311。《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疏》则不仅自毁无才,还自究过往:“臣在少年,粗心浮气,狂诞自居”;再加上为祖母尽孝的理由:“臣自幼失慈,鞠于祖母岑,今年九十有七,旦暮思臣一见为诀”,恳求:“退归田里”[36]316。总之,前前后后,共有十几通向皇帝的请辞报告,显出对社会的无奈失望与退隐的企求。
坚持中华学脉。这里的“中华学脉”,既包含对儒家正脉的理性坚守,也包含对道教佛教的灵性体验。“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中国古代学术,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以践履为特征的、信仰性质的学说,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严厉、持久而漫长的人格训练来确立道德的理想和人格的伟大信念。所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所谓‘正心诚意’(《大学》)、‘求其放心’(《孟子》),所谓‘格物穷理’(朱熹)、‘致良知’(王阳明),乃是针对心理训练而发;历代儒生都反对视道德为知识,故有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之分,有知行合一之说,其原因正在于道德的进步非知识所能解决[37]22……其实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儒、道、释——严格说来都不是哲学,而只是代表宗教的思维方式。作为宗教的思维方式,它们把主要工作放在人生的道德实践上,正因为如此它们几千年所做的事情都只不过是在追求对若干永恒价值的体验而已。”[5]353此外,王阳明时时静坐冥想,占卦卜筮,是具有道、佛宗教灵性的体验活动[37]。儒、释、道,历来都被认为是中华学脉。
代表时代,提出“心学”。王阳明的“心学”,可以说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普遍心态:崇尚白银与物质的市民社会中的集体无意识,普遍化地为商人与商业正名的思想,反思与反对宋人传统的学术、艺术风气,清醒的士大夫对时代的反思与批判等等。蒙文通曾指出:“讲论学术思想,既要看到其时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学脉渊源……可先论述当时的变化和风气,突出某些人物,如明代中叶正德、嘉靖以来,学术界就已逐步发生变化,产生了一种反对宋人传统的新风气,提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不读唐以后书的口号,从文学首先发动,蔓衍到经学、理学各个学术领域。王阳明正是在这一风气下起而反对朱学的……”[38]应该说,明代中期的“时代精神”,全面体现在文学、书法、绘画、市民小说等领域,而阳明心学,应该是其中鲜明的、理论的阐发。
对阳明心学的阐释历来其说不一,见仁见智。我们理解的“心学”核心内容是:“心即理”——(我的心)即是天理,而非宋理学所说天理在外。“吾心之良知,即天理也”[35]49;“知行合一”——真正的良知必需践履来证实,而非以学问为牟利工具,“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35]46;“致良知”——对良知,无论何时何地必须一以贯之地践履、坚守、完善与达成。“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32]111
三、余论
本文提出“生态哲学”,并非要在学术上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对当今现实世界里人类生态问题的回应。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几乎每一次讲话都不惜用最激烈的言辞痛陈人类面临的危机,关于自然生态的危机,他说:“我们必须结束这场向大自然发动的战争”,并且反思自己与人类生命保障系统的关系[39]。此外,法国百岁学者埃德加·莫兰、日本宗教哲学家梅原猛和企业家稻盛和夫、国内社会学泰斗费孝通等,都为当代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撕裂深感焦虑。因此,我们采用“生态哲学”这个概念,不过是站在常识的角度,凸显一种新的把握人类命运的世界观:人类是地球上亿万物种中的一种,是唯一能为所有生物负责的生物。人类自身的生存,有赖于适宜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但是,在“唯我独尊”“唯我独强”“唯我独富”等民族功利主义普遍存在的今天,既残留原始部落式的“丛林法则”,更加速给该法则提供着现代科技手段。于是,全球性的自然与人文生态形成急剧恶化的态势。用包含王阳明心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照人类,力倡“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伟大胸襟,弥足珍贵,是最值得当今中国学者坚守和弘扬的立场和观点。总之,以生物—生态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世界,就是我们提出“生态哲学”世界观的初衷。
此外,生态哲学不仅是一种世界观,还包含着一种新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中“人是自然存在物”,以及自然界、人类与精神活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为基础,顺应当代科学技术的高度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特征,以生命存在的极度复杂性为出发点,全方位、多学科、怀着对复杂性的敬畏感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六卷巨著《方法》的作者埃德加·莫兰在度过百岁后反思:“尽管自然、文明和人类以及所有地区的局势都在不断恶化,可生态意识的形成依旧呈现出极其局部化且非常缓慢的态势。”还说:“我意识到,我们所掌握的知识被分门别类地箱格化,却无法处理重大问题……我们不仅有必要重新审视马克思,不仅要借助新知识重新思考人、生命和世界,还有必要重新思考思想……于是,我走上了借助各种知识建构起复杂性知识和复杂性思维原理的道路。”[40]这种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观照问题的方法,就是我们理解的生态哲学的方法论。
于是,我们以此来分析王阳明及其“心学”,不仅关心思想观念,也关心自然环境;关心理性,也关心潜意识;关心精英与文本,也关心群体无意识及社会变迁;关心思想及其传承,也关注思想者的生物禀性;关心历史、思想史、社会心理等传统学科,也关心气候气象、生物遗传、物产资源、金融货币、军事制度等内容。显然,这就摒弃了传统布道、信奉、感悟的宗教思维方式,摒弃了动员、服从、追随的政治思维方式,也摒弃了传统经院哲学条分缕析、概念游戏式的思维方式。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也符合当代科学的结论,更能与当代现实生活与民众心态产生联系。
当然,要将阳明心学转化、运用到当下,不仅要分析明代中期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更要观察当今的全球与中国的自然生态,特别是复杂的人文生态。远离了一国的农耕经济、实物经济与消遣经济,融入全球化的工商经济、货币经济与消费经济主导的谋生方式;远离了乡土与熟人社会,进入由城市陌生人组合起来的当代多元社会组织秩序;远离了天地鬼神、祖宗儿孙观念下的全套神圣礼仪,采用世俗化、功利化的日常行为习俗秩序;远离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推己及人的群体观、克己复礼的自我观,普遍接受天人两分的科学自然观、个体利益为主的群体观、自我中心的自我观……在这个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如何将古代的、书本的、精英的阳明心学转化运用到当今的、现实的、百姓的生活与心灵,尚待理论与实践的深入研究。
此外,阳明心学几个重要命题运用于当代,如“心即理”,就要与认识论、与神经认知科学之间进行有效的连接,就需用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理论进行认真有效的剖析与整合,才可能将古人的精彩思想有机地“拼图”融入当代的“世界图景”中,最终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最后,需要说明,我们一直想用这个“生物—生态—生态哲学”的三维理论框架,来重建整个贵州的历史面貌,揭示贵州文化的生态智慧及其当代价值。本文,只是该课题的一个小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0.
[4]恩斯特·麦尔.这就是生物学[M].涂可欣,译.台北:远见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21:44.
[5]方朝晖.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2.
[6]塞缪尔·阿贝斯曼.为什么需要生物学思维[M].贾拥民,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98.
[7]蒋高明.怎样理解生态与生态系统[EB/OL].(2017-02-17)[2024-12-01].https://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7-02-16/130967.html.
[8]罗勃·德赛尔,等.欢迎走进微生物组:解密人类“第二基因组”的神秘世界[M].张磊,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Ⅻ.
[9]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
[10]何玉宏.生态哲学对社会学的影响与启示[J].求索,2007(1):142.
[11]王立铭.生命是什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8.
[12]陈来.有无之境·绪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3.
[13]承现峻.连接组:造就独一无二的你[M].孙天齐,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7-8.
[14]蓝勇,编著.中国历史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61.
[15]李伯重.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化与人口变化[J].人口研究,1999(1):15-19.
[16]吴光,等,编校.补录六//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四十四[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17]窦德士.长城之外:北境与大明边防 1368-1644[M].陈建臻,译.北京:天地出版社,2004:371.
[18]王蕊,花琦.明代“九边”军屯衰落原因考察——从环境视角出发[J].商业文化,2011(8):127-129.
[19]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112.
[20]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M].北京: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001.
[21]万明.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47.
[22]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J].暨南史学辑刊,2003:276-309.
[23]吴思.隐蔽的秩序[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116.
[24]赵轶峰.明代经济的结构性变化[J].求是学刊,2016(2):140-152.
[25]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26]王锜.吴中近年之盛//寓圃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42.
[27]张邦建.明代中后期奢靡之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7(7):1-4.
[28]叶康宁.明代中晚期的社会风气对书画交易的影响[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9(4):55-59.
[29]章忠民.货币:一种人学的读写[J].学术月刊,2003(8):12.
[30]张锡勤,柴文华.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33-136.
[31]柴艳萍.货币、异化与社会转型——马克思的货币伦理思想探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4):76-81.
[32]吴光,等,编校.语录三//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三[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33]吴光,等,编校.外集三//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二十一[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852.
[34]吴光,等,编校.文录一//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四[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174.
[35]吴光,等,编校.语录二//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36]吴光,等,编校.别录一//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九[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37]杨一清.杨一清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1034.
[38]蒙文通.甄微别集·治学杂语//蒙文通全集:第六卷[M].成都:巴蜀书社,2015:25.
[39]古特雷斯.必须结束向大自然发动的战争[EB/OL].(2023-05-22)[2024-12-01].https://news.un.org/zh/story/2023/05/1118157.
[40]埃德加·莫兰.一个世纪的人生课[M].徐杰译,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4:12-142.
【刊载信息】顾久,胡海琴.三维生态观下阳明心学的发生论——阳明文化转化运用的新理论框架[J] .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4):2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