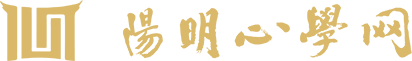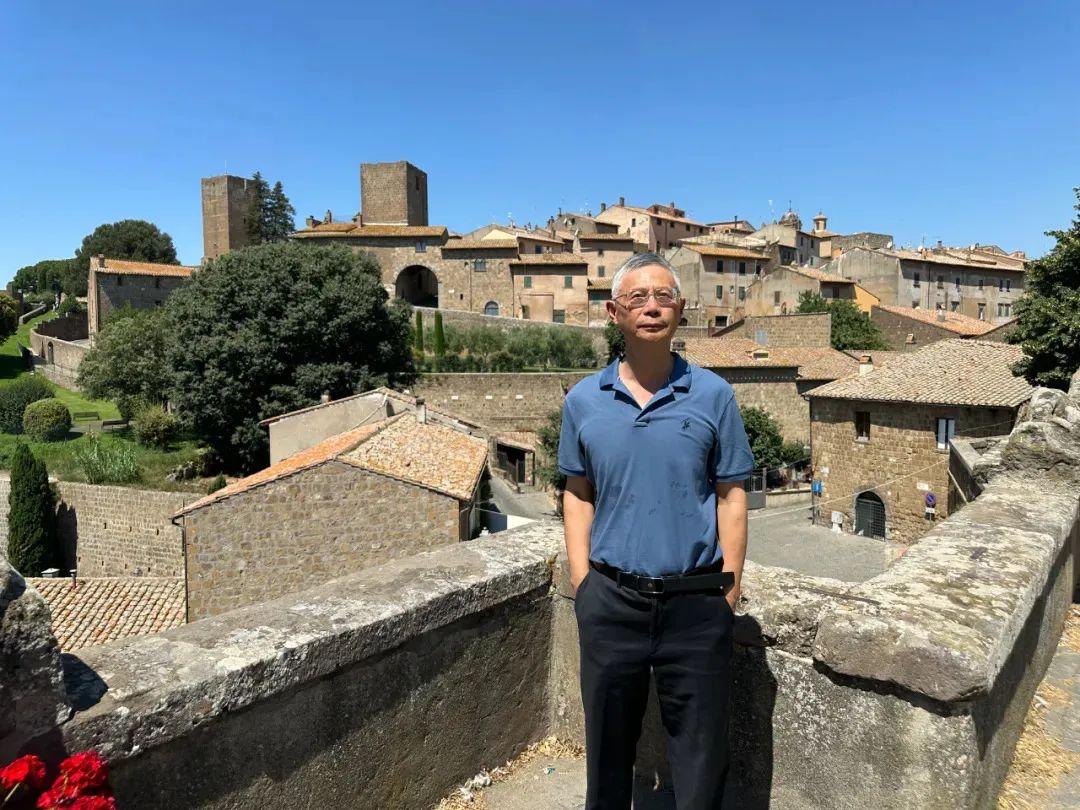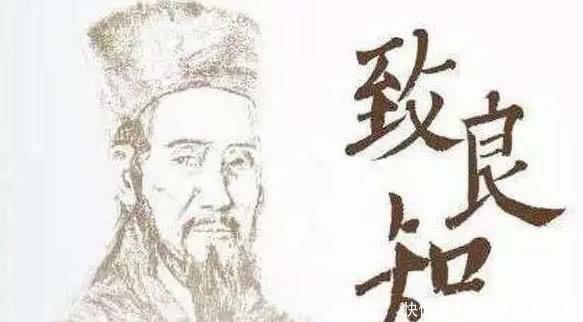《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作者简介
欧阳祯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杨永涛,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民本思想是陆九渊心学的核心指向,它的政治向度从心学母体中孕育而生,转进为一种具有平民精神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理论范式。陆九渊将“本心”提撕到“天理”的哲学高度,以“人无贫贱皆向善”的悲悯情怀彰显“不识一字,亦还我堂堂地做个人”的人学立场。陆九渊从理势之辨、君臣之分、君民之义等多个视角构建起以生民关怀为理论诉求的政治哲学和以政治向度为核心表征的民本思想。以“从心性到政治”的阐释理路进行分析,陆九渊民本思想的政治向度体现在政治理念、政治实践和政治教化三个层面。由此,陆九渊民本思想的现代诠释得以深构。
关键词
陆九渊;本心;民本思想;政治向度
目次
一、从心学母体中孕育的民本思想
二、政治理念层面:以理统势,置吏为民
三、政治实践层面:荆门之政,必正人心
四、政治教化层面:讲义代醮,心正得福
五、结语
陆九渊的心学是宋代儒学的一座高峰,与朱子学相互激荡,是阳明心学的理论先导,呈现出体用一贯的心学品格。陆九渊的民本思想熔铸于心性学与政治学之间,他的仕宦生涯体现了他对人心的把握和对事实的探明,是象山心学的彰显[1](P37),换而言之,象山在治事为政上所表现的作为,是从“本心”发用流露出来[2](P174)。同时,这种心学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诗化境界和践履之美[3](P199),但这种诗化境界和践履之美并非远在瑶池,它具有庸常性,这是因为陆九渊思想中的“本心”范畴是一种普遍性、客观性的主体存在,并由之启导出“心即理”的理论高地。陆九渊通过此心与此理的同构,开发出民本思想中的人学意涵并将之应用于实践。在具体实践中,基于心学“自反而缩”的自觉精神,陆九渊大刀阔斧地进行地方改革,并进行政治教化,这促使荆门产生了显著的社会风俗变易,对民众的“本心”起到提撕和触发觉醒的功能,产生了民风醇美的社会效果。
那么,如何阐释陆九渊的民本思想,尤其是作为具备鲜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特质的大儒思想,必须采取一种富有效验的诠释理路。“从心性到政治”的阐释理路立足于“与命与仁”的儒家哲学核心范畴,强调深度挖掘传统思想家本人的人学思想,通过研究思想家对于天人之际的哲学思考、对于身心关系的人格修养、对于社群政治的理论与实践等面向,主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结合思想家的哲学风貌以意逆志,对个案的政治哲学的思想来源、呈现向度、理论价值等持中而论。这是一条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富有积极现代意义和文化使命感的阐释进路,这也是笔者多年来从事先秦哲学和陆王心学研究的重要路径。笔者曾仔细考察了陆九渊的家风家教、心学理论、哲学境界、学派建设、地方实践等方面,但如果要全面地、细致地总结陆九渊的民本思想,则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和深究。从整体学术风貌上看,诠释陆九渊的民本思想,应把握住政治向度这一核心诉求,而理解陆九渊民本思想的政治向度则需要通过“从心性到政治”的诠释理路进行勾勒。这就必须重视心学思想的母体在其民本思想产生、发展、成熟中的导向性功能,通过平民精神的视角切入陆九渊民本思想的研究之中,并由此呈现出陆九渊民本思想政治向度的三大层面。
一、从心学母体中孕育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精华,理解“民”义是解读民本思想的第一把钥匙。就“民”的本义而言,据甲骨文、金文等早期文字资料,“民”字的字形为棒型物竖向插入人的眼睛,本义实际就是目盲[4](P180)。《说文解字》解释为“民,众萌也”,《康熙字典》进一步解释为“言萌而无识也”,合而言之,萌是指草芽,初生的嫩芽如同一张白纸,以此作比,民也就是指懵懂且需要通过教育得以“成人”的人。现代社会中,一般意义上的民众,都是具有共同的生存权利与道德权利的主体,是具有平等性、普遍性的人权个体,这其实也是现当代新儒家构建思想学说的重要指向。传统儒家心性学说承接孔曾思孟以性善论为主调的学术理念,基于此种理念,陆九渊眼中的民众至少应当具备两个特质:第一,反映在思想道德领域之中,拥有普遍平等的道德权利是民众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前提,即《中庸》“天命之谓性”的第一层要义;第二,在现实层面,封建王朝中确保平民平等生存权利的健全制度保障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导致士大夫开始由“得君行道”转向“觉民行道”以此表达内心的“外王”诉求,在这一过程中士大夫也看到了民众之“私欲”遮蔽了“本心”之纯粹至善,进而推进了宋明新儒家的理论革新和地方实践。进而,明末清初思想家对于民众和社会的思想启蒙已经不仅仅是思想道德层面关于平等意愿的诉求,还体现在对政治制度改革的探索。由此可概观,在传统中国发展进程中,对“民”的认识与思想家自身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要加以扬弃,正视其中的历史局限。同时,以孔孟儒学自身特质的视角来看,对“民”权利的维护、保障和发展是中国传统儒者所学习、实践和体证的民本思想之主线、主轴,这背后是不忍人之心、四端之心。
首先,心学主张每个主体在人性善端本自具足层面上的平等性,这是阐释心学家民本思想不容忽视的理论根底。具体到陆九渊心学上,他继承发展了孟子的“本心”说,以“心即理”的诠释强化了“心”的哲学高度和形上学意义。牟宗三认为,“本心即理,这本心之自律与自由乃是一具体而真实的呈现”[5](P8)。“自律”与“自由”同为心体的呈现,存养“本心”乃是实现由肉体到精神真正自由的核心路径,甚至是根本性的途径。因此,陆九渊强调“发明本心”的修养工夫,莫若以明,通过敞现“本心”的生发机理、活动过程、价值导向,并由此显发出“本心”思想在天人之际的超越性维度,将其作为设计地方政教制度的根本性理论依托,试图唤醒每个生命体的良知良能。简而言之,陆九渊寻求的是“人”的自由。郭齐勇进而指出,“‘本心’乃一道德情感、道德法则、道德意志的统一体,它并非人的一种生理意义、心理意义以及社会学意义的心,而是为每个人所本有、具普遍性与恒久性的‘同心’或‘大心’”[6](P390)。陆九渊的“本心”也就是对孟子所言“不忍人之心”与“四端之心”的具体呈现和理论凸显,我们借助“本心”的概念审视自我存在的意义,且反思人我、人物(人事)、天人等关系的时候,“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一道德起点上的平等性更清晰地显现出来了。“我”与古圣先贤之心乃是同一颗心,这不是一种生理意义上的,而是一种超越意义上的,十字打开,贯通时空,哪怕是一个贩夫走卒面对圣贤,亦是同然,这也是王阳明所言“精金之喻”的密钥所在。因而可以说陆九渊的民本思想,尤其是其思想中深沉的平民精神基调,正是从他的“本心”主体性上豁显而来。
其次,这种儒家心学的平民精神显发在陆九渊民本思想的主客两面均能得到证实:在主体方面,陆九渊以“主民”二字作为民本思想的纲领,多次强调士大夫群体应当推己及人,重义轻利,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单虹泽认为这对晚明“觉民行道”的思潮有一定的影响[7](P12)。相较于阳明和阳明后学,尤其是泰州学派而言,陆九渊的民本思想对于士大夫“行道”层面的启发确实起到先导的意义,尤其是他强调“六经”为“我”“注脚”,更是打破了一般意义上士大夫对经典权威的畏缩感,陆九渊所言的“我”乃是一“大我”,当然具备一定的超越性,“注脚”并非简单的主客二分,重要与次要二分,更多的是强调经典是每个个体(尤其是士大夫群体)生命存在中不断得以体会、体悟、体征的沟通对象,而非唯一的权威性验证。陆九渊重视的是生命个体与现实世界相互摩擦的真实感,也就是实学意义上的真知真行,这就启发了士大夫阶层要真正地在寻求自我意义的过程中践履圣贤之道,而非空谈议论,这与南宋时期多数士大夫的心态是不同的。在客体方面,从陆九渊学说所面向的对象看,陆九渊的讲学多面向平民百姓和底层士人,这亦是他思想平民精神基调的又一个侧证。陆九渊倡道南宋时,弟子以数千计,在与他相关的文集、地方志等文献中,记录在册实有一百七十六人[8](P4)。从象山弟子与门人的数量和比例上看,象山门人也是平民居多。郑朝晖也指出,“陆九渊的赠言对象皆是与其亲近之人,多为其乡人。无论是士人、僧仆、百姓,皆与他共同形成了一个公共语言空间”[9](P504)。这种植根于基层民众的心学思想更具亲和感,与朱子学说多以导向精英阶层稍有不同,这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陆九渊从小所处的生活环境。长期的、大家族式的生活情境,意味着陆九渊从小在父亲、兄长们的熏陶下,善于与底层群众交际,善于体会底层群众的心理状态,善于在家族管理中把握如何促进人与人的稳定和和谐。综合来说,陆九渊的民本思想及他对儒家平民精神的高扬,与他对世事人心的把握密不可分,与他的学思特质密不可分,与他对民众的悲悯情结密不可分,这也为王阳明及其后学的民本思想的主体性、丰富性、多元性提供了思想先导。
整体上看,陆九渊的民本思想以“本心”为内核的心学思想衍生出来,他极为重视“人”存在的权利、意义与价值,并由此派生出民本思想的政治向度。第一,在政治理念上,陆九渊高扬“天理”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凸显“天理”与“本心”的交融,破除人们心中对“世势”的迷障,强调以民心作为衡量施政水准的最终标准。在重视制约君权的思想之外,陆九渊还极为敏锐地洞察到“胥吏”作为政令通行的最后一站,需要加以引导和警戒。他认为,胥吏作为底层官员应当充分尊重民意、厚养民生,做好政令的最后一道桥梁,杜绝欺上瞒下的追逐私利的行为。第二,在政治实践上,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在湖北荆门度过。陆九渊推行的荆门之政立足于南宋荆门的内外实情,体现德主刑辅的政治操练,注重通过亲施政令和公共事务等途径团结民众,“制民之产”,由此推进了南宋荆门内政外交的和谐与稳定,这体现了陆九渊融贯心学思想与政治实践。第三,在政治教化上,陆九渊对民众的道德主体性来源予以揭橥与肯认,注重以儒家的“正心”之学教化民众,主张人人可以通过诚意正心的天人交感获得上天的护佑和赐福。凡上述种种,无不是由“本心”的精神力量启导出来。我们亦可从中体察到陆九渊民本思想政治向度的仁爱、博厚与醇美。
二、政治理念层面:以理统势,置吏为民
陆九渊民本思想最突出的特质是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并通过对“理”与“势”关系上的讨论,高扬此“理”的价值绝对性和历史超越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陆九渊思想中的“理”更具有一种博施于民的悲悯情怀。“理同”落实到人心之中便是“心同”,人人具足的“本心”在政治向度中的普遍存有意味着“民心”的地位与意义。这里主要可以从政治合法性、君民关系论、吏民关系论三个角度分析。
第一,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看,陆九渊在《常胜之道曰柔论》中提到,“理可常也,而势不可常也”。天理的普遍性和恒常性与时势的周期性和短暂性是形成鲜明对比的,综观古往今来,即便许多杰出的政治家,也“往往徒恃其有胜之势,而不知其无胜之理。六国并而秦以破,南北混而隋以亡,此恃胜之势,而不知势之不可常也”[10](P360)。秦、隋两朝虽然有一时的胜势,但统治者只依赖威势而置人心之“理”于不顾,最终二世而亡。因此,陆九渊总结道:“窃谓理势二字,当辨宾主。天下何尝无势,势出于理,则理为之主,势为之宾。天下如此则为有道之世,国如此则为有道之国,家如此则为有道之家,人如此则为有道之人,反是则为无道。”[10](P168)在这里,陆九渊对理与势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说明:理对势具有统御作用,势应当符合理,只有理势相协的举措才是合于天道的。他进一步由天下之道洄推到国家之道、家庭之道和个人之道,这既是在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合法性的问题,也是在讲个人“修道”层面的“天命之谓性”背后的“本心”问题。人如果“无道”,那就是“失其本心”。
第二,将“以理统势”的思想落实在君臣关系论中,陆九渊认为,“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却知人主职分”[10](P403)。象山认为,君主应当把民众作为社稷存在的根本,应当明确政治举措的利益导向是民众,而不是君主自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故君者,所以为民也。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10](P274)君主之所以为君主是为了保养民众的生息,使之“成人”,而且是要对天负责,亦是对“天理”负责。人成为君主,只是时势的偶然造化,只有保持在“天理”层面上具备了合法性,君主之世势才可能是“正”的。具体而言,“民生不能无群,群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生不可以保。王者之作,盖天生聪明,使之统理人群,息其争,治其乱,而以保其生者也。夫争乱以戕其生,岂人情之所欲哉?彼其情驱势激而至于此,未有不思所以易之者也。当此之时,有能以息争治乱之道,拯斯民于水火之中,岂有不翕然而归往之者?保民而王,信乎其莫之能御也”[10](P382)。陆九渊在这里强调“保民而王”,他承认社会存在个体之间的矛盾关系,小到社群之内的争斗,大到国家之间的战乱,这一切原本并非人情中本有的诉求,而是情势对本心的误导,其后果则是民众互相争斗,生息难以为继。因此,站在有国有家者的角度看,要想使人民得以保养生身和“发明本心”,君主就理应平息争讼,导善救乱,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秩序作为奋斗目标。君王作为“天子”应当“统理”,也就是“以理统势”,爱民保民,势合于理,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现在看来,这里面的问题还应涉及对民众权利的制度性保障和包含君主在内的全民司法体系的健全,不可否认,陆九渊的政治理念有其历史视域的局限,需要加以扬弃。同时,陆九渊主张士人群体应当践履圣人之学,匡扶、纠正君主的过失,陆九渊认为《孟子》里“幼学之,壮而欲行之”中“行之”是指“行其所学以格君心之非”,并且“引其君于当道,与其君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使斯道达乎天下也”[10](P26)。此道就是指天理,天理通过士大夫的揭橥和指引,运化于君道,则即是明道。这里有宋代士大夫与天子“分权”的意味,不过绝大多数统治者并不会买账。除了通过“格君心之非”外,陆九渊还提出以“任贤、使能、赏功、罚罪”[10](P496)四法作为医国的“四物汤”,旨在让君主明其理,实际上也是试图以“天理”统御君主“世势”,从而达到理想化的王道昌明,目的是使得百姓得到福祉,社会得到有序和谐。
第三,在吏民关系论上,陆九渊认为官吏是上下沟通君主与平民的桥梁,主张官吏应当负有天下情怀和社会担当。“是故任斯民之责于天者,君也;分君之责者,吏也。民之弗率,吏之责也;吏之不良,君之责也。书曰:‘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又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此君任其责者也。可以为吏而不任其责乎?”[10](P229)陆九渊认为,在君主—官吏—人民的科层中,官吏作为君主的延伸而直接面对基层民众,他们应当共同承担君主的责任,也就是向民众直接负责,并与之保持融洽的相处氛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张官置吏,所以为民也。‘民为大,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邦本,得乎丘民为天子’,此大义正理也。”[10](P69)这里提到,君主对上天负责的途径是保障民众的合法权利。官吏要协助君主分担政治责任,因而君主与官吏的社会责任是一致的。在这里,“天、君、吏、民”四者构成一个责任伦理体系,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理论。但陆九渊在这里也强调的是官吏应当承担起相应的政治责任,这就涉及到官吏对谁负责的问题。陆九渊指出,“民为大”,民众是国家和政权的基石。陆九渊在这里显然更强调官吏要对民众负责,而非以向君主负责重要。这种民本思想在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现实冲击力。
相较于官而言,吏对于民众的现实权利而言,影响更多。陆九渊尖锐地指出官与吏的不同之处:“官人者异乡之人,吏人者本乡之人。官人年满者三考,成资者两考;吏人则长子孙于其间。官人视事,则左右前后皆吏人也。故官人为吏所欺,为吏所卖,亦其势然也。吏人自食而办公事,且乐为之,争为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无良心,无公心,亦势使之然也。”[10](P112)宋代统治者为了防止出现唐末的地方割据,他们在官员调用上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而底层胥吏则根深蒂固,长期在本地生活。胥吏的贪墨私欲无论对于百姓而言,还是派遣到地方的官员而言,都是政治顽疾。陆九渊认为,胥吏不知所谓仁义于何处,只求私利,不顾公义,这同样是恶劣的政治生态所造就的。陆九渊在与友人们的书信中也透露出胥吏贪污腐败的程度:“大抵吏胥献科敛之计者,其名为官,其实为私。官未得一二,而私获八九矣”[10](P55),“今之贪吏,虽在利源优处,亦启无厌之心,搜罗既悉,而旁缘无艺,张奇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横索,无所不至”[10](P73)。这应是陆九渊在基层真切接触到的实情。其实,陆九渊的生活背景以及“十世义居”的大家族的管理方式以及他在基层的生活环境决定了他从小长期与底层官吏接触。在他的观察与日后的政治实践中,他指出,比起官员来,胥吏腐败是危害社会底层更大的毒瘤,因为胥吏的“本心”已经被他们自己的私欲放逐掉了,因而,底层胥吏之“势”只是个“利势”,必然“不可常也”,政治秩序必将走向动乱。陆九渊也曾痛心地指出,“凡事不合天理,不当人心者,必害天下,效验之着,无愚智皆知其非。然或智不烛理,量不容物,一旦不胜其忿,骤为变更,其祸败往往甚于前日”[10](P223)。胥吏作为直接与底层民众接触的“势”,他们如不能以“理”统“势”,唤醒自己的“本心”,政权公信力必然从基层开始土崩瓦解。陆九渊来到荆门之后,胥吏也就成为政治治理实践中的重点。
在传统儒家修己安人的追求中,理念需落实于实践方能彰显其背后的核心诉求和现实意义。从理念的思辨迈向具体的政治实践场域,陆九渊在荆门的施政举措成为其民本思想生动且深刻的注脚。荆门之政不仅是其政治理想的试验田,更是其“必正人心”[10](P425)民本理念的有力践行,从中可洞察其如何将抽象的政治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治理策略,推动社会风俗的变易与民众道德的觉醒。
三、政治实践层面:荆门之政,必正人心
从“本心”到“民本”,陆九渊的心学修炼与他的政治实践密不可分,二者在道德意识和道德政治实践中存在重要的内在关系[11](P69)。传统儒家的“人道”与“政道”的关系也是如此,陆九渊对《中庸》“人道敏政”的解释是“果能尽人道,则政必敏矣”[10](P472)。这里强调的是“尽人道”的前提性和优先义;朱子解释为“以人立政”如同树苗成长般成效显著,“人存政举,其易如此”[12](P29)。这里强调的是重视“人道”的简易性和生成义。象山更强调为政者要“先立乎其大”,扩而充之,以“人道”的心性锤炼推进“政道”的风清气朗。从“人道”推扩到“政道”,由“政道”反溯于“人道”,这是陆九渊民本思想政治实践的核心路径,也是“从心性到政治”的致思之路。
从陆九渊生平的“人道”经历来看,纵观陆九渊的生平遭际,他一生所担任的职务并非高官,早年不得重视,后来逐渐淡出统治者的政治视野,他也由此反思“得君行道”是否是实现政治抱负的理想途径。之后的时间,他在象山讲学,学术随之日臻成熟。光宗继位后,他接到了知荆门军的任命,绍熙二年九月他正式抵达荆门,开启了他人生最后一段为政之路,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他让荆门的政风、民风得以改善,核心主张是“必正人心”,最终导向是民众的自我觉醒,“觉民行道”的士大夫自觉促成了他民本思想的最后实践。荆门之政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始终践行儒家的“修己安人”之道,“尽人道”。
从陆九渊荆门为政的“政道”举措来看,陆九渊亲自参与了治理荆门的每一个重大环节,最根本的价值指向是“人无贵贱皆向善”。通过立足于“本心”的施政准绳,陆九渊着重从对外、对吏、对民三个领域治理荆门,改善了当地民风,获得了百姓和士林的称赞。
第一,陆九渊重视南宋荆门地区的安全形势,他初到荆门便详细观察地理风貌,由于荆门地理位置和战略地形的重要性,他意识到必须建筑城墙以做防御,抵挡金军的南下。他通过核算成本,节省开支,广泛号召,“躬自劝督”,借此事务对荆门民风有了实践层面的体察。同时,他十分重视操练军队,“勇者不惧”,这与他少年时的经历相关。“先生少时闻靖康间事,慨然有感于复讐之义。至是访求智勇之士,与之商榷,益知武事利病、形势、要害。”[10](P496)他在荆门时,“平时教军伍射,郡民得与,中者均赏”[13](P12882)。而且做到了治军严明,操练得当,严明军法,使得民众有了一个相对安全、安稳的生活环境。这两点实际上都是从地方安定的对外因素进行政治实践,“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陆九渊将他的民本理念应用到地方军政之中,这与孔子的主张不谋而合。
第二,在意识到胥吏是地方行政中的顽疾后,陆九渊十分重视荆门内部的吏治建设,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公共政治的平稳运行,更重要的是唤醒地方胥吏的“本心”。以“政道”的赏罚分明促使胥吏的“人道”觉醒。他看到“簿书捐绝,官府通弊”的怠政,于是“方令诸案,就军资库各检寻本案文字,收附架阁库,随在亡登诸其籍,庶有稽考。若去秋以来,文案全不容漏脱矣”[10](P214)。这样,一则重塑了官吏的责任心,提撕了他们的是非之心和羞恶之心;二则使得一切都有据可查,促使官吏不敢贪墨。同时,陆九渊赏罚分明,敢于惩处贪墨官吏,“今乃以告讦把持之名而抑绝之……惩一二以威众,使之吞声敛衽,重足胁息,而吾得以肆行而无忌”[10](P69)。进而用以“仁义”为核心的政治责任感转变了当地官吏的恶浊作风,使得官吏们视官事为家事,这也是“从心性到政治”的题中之义:“初习俗偷人,以执役为耻,吏为好衣闲观。至是此风一变,督役官吏,布衣,杂役夫佐力,相勉以义,不专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无事。”[10](P509)陆九渊整顿吏治的同时,在经济领域废除三门引和只能用铜钱交税的规定,既减轻了百姓的经济损失,又激活了当地的商业发展,也提升了府库的收入,这是陆九渊熏习“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的重要表征。
第三,在处理好社会内外秩序的基础上,陆九渊善于活用心学教法以平息民众纷争,他继承了孔子“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的社会治理目标。陆九渊始终坚信孟子的“四心”说,杨简曾因“扇讼”对陆九渊佩服之至,遂拜师门下。在荆门,象山的断讼依然是直察人之“本心”,依据“是非之心”进而断讼:“有诉人杀其子者,九渊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无恙。有诉窃取而不知其人,九渊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讯之伏辜,尽得所窃物还诉者,且宥其罪使自新。”[13](P12881)由此可知,其一,陆九渊善于处理社会矛盾,断案如神;其二,之所以断案如神,是因为陆九渊对老百姓们十分了解,是真正地行走在社会底层的公仆;其三,陆九渊在荆门的为政举措可谓是全方面的,他善于把握民众的心态,及时了解他们的疾苦,善于和汲汲于名利的胥吏作斗争,因而阖境安宁,社会风气逐渐变得醇美。
陆九渊荆门之政中的实践智慧,正是“人道”与“政道”时刻互动的生动注脚。他的荆门之政亦获得称赞。杨简指出陆九渊在荆门期间“教民如子弟,虽贱隶走卒,亦谕以理义”[10](P390)。陆九渊走遍荆门,把他的心血全部用到当地民众身上,“逾年,政行令修,民俗为变,诸司交荐。丞相周必大尝称荆门之政,以为躬行之效”[13](P12882)。这样的政治效验得益于陆九渊对“人道”的深切把握,也是其民本思想“从心性到政治”体用一贯的体现。黄岳曾赞叹道:“先生之学,正大纯粹。先生之教,明白简易。其御民也,至诚之外无余术。其使人也,寸长片善,未始或弃。”[10](P513)陆九渊把学问熔铸到生命之中,先立乎其大,以“至诚”之心唤醒人的善心善念。正如陆九渊自述:“此间风俗,旬月浸觉变易形见,大概是非善恶处明,人无贵贱皆向善,气质不美者亦革面,政所谓脉不病,虽瘠不害。近来吏卒多贫,而有穷快活之说。”[10](P512)陆九渊肯认每个人都有善端,并善于启发施教,效果往往一针见血,能够直指人心。他的为政措施多是基于对人性的考量,这里面有两层意涵:一是对人之天性本善的唤醒;二是对后天私欲的剥离。无论百姓,还是官吏都对此“中心悦而诚服”(《孟子·公孙丑上》),即使是胥吏沦落到贫困之地,也可以体会到一点儿颜子之乐的“穷快活”,诚然一幅泰和景象。
陆九渊指出:“古者无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严;后世有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略。”[10](P393)他和孔子一样,力图打破现实中因个体社会地位不同而导致的人格地位的区分,他将人的德性平等视作衡量一个人是否“成人”的首要标准,同时,他也讲“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10](P395)。“本”,也就是做人的根本,依照“本心”的标准做人做事,反对盲信盲从,尤其是要谨慎地对待来自权威的力量,这具有很浓厚的主体意识和平民精神。陆九渊在荆门的政治实践,通过一系列切实有效的举措,成功地稳定了社会秩序,为荆门地方治理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政治教化层面:讲义代醮,心正得福
从儒家政治哲学的深度审视,政治治理不仅在于外在秩序的构建,更在于内在精神的教化与自我觉醒。当社会秩序得以稳固,陆九渊将目光投向更深层次的政治教化领域。行仁政必待教化而始完备,而善教亦是执政者得民心之不可或缺的手段[14](P258)。在传统政治生态中,政治教化是维系社会道德规范、传承核心价值观念的关键环节。陆九渊以《荆门军上元设厅皇极讲义》为重要载体,深化了其在政治教化层面的探索,旨在从根本上提升民众的道德觉醒与精神自立,这是一篇关于陆九渊民本思想的纲领性篇章。
陆九渊主张要保持对天命的信仰,“无事时,不可忘小心翼翼,昭事上帝”[10](P455)。这种谨慎的精神,源于周初的“敬德”等观念,是一种充满责任感的忧患意识。从把责任、信心交给神转为自我担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种由警惕性而来的心理状态,具体表现为精神敛抑集中,对政务和事业谨慎、认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同于宗教的虔诚。这不是消解主体性而是自觉、主动、自省地凸显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14](P20)。绍熙三年正月十三日,按照荆门当地的旧历,须行作醮仪式,这是当时道教信仰的一种体现。而陆九渊选择以讲义代醮,专讲《尚书·洪范》的“皇极畴”,这不是日常一般意义的平民教育,而是带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尚书·洪范》载:“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皇极”二字何解?陆九渊继承了郑玄的“大中”的解释;而朱熹则以“人君之标准”解释皇极。又因为陆九渊在荆门作《荆门军上元设厅皇极讲义》晚于朱子的相关论述,所以,陆九渊这篇讲义似有针对朱子所论的意味。笔者更关注的则是陆九渊的民本思想如何在此讲义中呈现,以及其中“觉民行道”的民本思想。
首先,陆九渊认为“皇极”乃是一理,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福如何锡得?只是此理充塞乎宇宙。”陆九渊认为,“古先圣王皇建其极,故能参天地,赞化育。当此之时,凡厥庶民,皆能保极。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10](P284),这里刻画了一种与圣贤同行的和乐景象,实际上是给予了所有人以“极”的道德保障,是立足于尧舜时代理想化的民本思想蓝图,具有普遍意义。同时,“皇建其有极,即是敛此五福以锡庶民。舍极而言福,是虚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极也。凡民之生,均有是极,但其气禀有清浊,智识有开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古先圣贤与民同类,所谓天民之先觉者也。以斯道觉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极也,即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也”[10](P284)。“极”来自上帝,具有超越性和统御力。《讲义》还提到君主“建极”与生民“保极”的君民互动,推动了政权的稳定,而上天赋予的德性光辉照耀在每个生民身上,“人极”(也可理解为“善端”“本心”)的觉醒与上天即刻便有了超越性的互动,但因为平民气质差异,因而感应不同,因此,需要先知先觉的圣贤来“道夫先路”(《离骚》)。同时,陆九渊对君主之“圣天子”形象的神圣化塑造,一方面彰显了天道的权威,另一方面看,这也增强了君权的地位,现实中难以形成对君权的制度化约束,需要反思和警惕,但陆九渊的最终导向还是希望民众得到教化和觉醒。
其次,陆九渊创造性地诠释出“心正得福”论。他认为,“实论五福,但当论人一心”。皇极之赐予的五种福德根植于人之“本心”,“此心若正,无不是福;此心若邪,无不是祸”[10](P284),这里陆九渊显然将《洪范》与《大学》合释,“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礼记·大学》),一个人如果不注重根源性的道德修养而误将外在的欲望视作福泽,必然如镜花水月一般难以得偿所愿。因此,“但自考其心,则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随形如响应声,必然之理也”[10](P285),这种“念虑”的端正与否,往往在顷刻之间,宜戒惧不已。陆九渊也曾说:“念虑之不正者,顷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虑之正者,顷刻而失之,即为不正。有可以形迹观者,有不可以形迹观者。必以形迹观人,则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绳人,则不足以救人。”[10](P488)这还是强调“念虑”的发动与本心的感应是瞬间而至的,念虑的正与不正如同王阳明所言的“良知”一样,是自知自明、当下即断的。同时,陆九渊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念虑”往往深藏在人主体的内心之中,客体并不能全然观察到,有的“念虑”可能表现出来,成为现实情境中的行为,有的“念虑”可能没有表现出来。孔子说:“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陆九渊的态度则更为谨慎,他进一步指出,通过行迹(包括语言)观人同样容易流于表面。这是不是陷入了一种对他人的不可知论呢?陆九渊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但他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以条条框框要求他人坚持道德操守,而不是从“发明本心”的根本角度出发,他人也不会真正信服和觉醒。阳明亦认为“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15](P103),人只要一息尚存,便有意念的生发。“意诚而后心正”(《礼记·大学》),心正则福自天降,这里面蕴含着一种“自反而缩”的内省意识,这也是一种“觉民行道”的儒家伦理表达方式,蕴含着“其心正,其事善,虽不曾识字,亦自有读书之功”[10](P285)的“本心”道德自醒意识。此外,陆九渊上元节此讲的另一目的是反对救赎宗教的迷思。当时的部分儒者认为,象山心学吸收了禅宗的心性思想,以至于将象山心学与佛教混为一谈;然而陆九渊明确指出,“愚人不能迁善远罪,但贪求富贵,却祈神佛以求福,不知神佛在何处,何缘得福以与不善之人也。”[10](P285)他的学说与当时民间流行的净土宗等救赎宗教之间,无疑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同时,这也意味着陆九渊始终把儒家“修己安人”“内圣外王”的观念融入自己的身心世界和人伦物用之中,他认为真正的“善”一定要在此岸世界中显发出来,人之所以为人,不能因为现实的遭遇而放弃对“善”的信心。他通过对“善”(“本心”)道德先在的阐释,重视化解人在义利之辨面前的道德紧张,旨在凸显德福一致的儒家方案。
五、结语
陆九渊的民本思想是一种植根于人先天道德禀赋的人学,“本心”的意义在于彰显人作为“三才”之一的高贵与尊严。一个人只有通过内心的道德自律,才能通向真正的自由之境。陆九渊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这种通过界定人自身存在时空之中,又可涵容时空的理论建构是一种深度的人格自由。儒家民本思想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思考如何加以扬弃的问题。我们反对传统帝制对普通人权力的剥夺,对普通人自由的践踏,对普通人生命的蔑视。陆九渊的“本心”思想实际上高度肯定了人自身的现实权利,无论是政治理念,还是政治实践,抑或是政治教化,这一思想始终主张作为一个普通人,他的生命来自天地人之间的精妙造化,神圣不可侵犯,他的道德权利来自先天的禀赋。人应当在后天“收放心”,把德性修养视为获得幸福感的最大归宿,这不影响作为人生存的物质利益的获得,相反,这恰恰建立在对人生存权利的保障之上。
陆九渊的民本思想通过“政治”向度三个层面逐步展现开来,这里面始终贯穿着一种儒家的平民精神。儒家的平民精神自孔孟以来,鸢飞鱼跃,生生不息,成为儒学当代转化、返本开新的重要思想资源。陆九渊的平民精神具有心学的思想背景、具体的实践路径、深沉的现实关切,实际上为阳明心学的平民精神如何进一步展开,起到了理论先导的作用。这种平民精神昭示着人要通过后天的“学而时习之”,体会、体悟、体证到人之所以为人“天爵”,这个过程是一种对自我真实存在的认知不断提升的过程。这一过程赋予了现实中所有的人以“可学可至”的权利,自我的生命存在因为有了具备现实感的“学”而充满了对未知一切的探索欲,进而体现为一种基于人自身发展的活泼泼的创造力。儒家的成人之道也就是由此逐步显露,通过自我对于圣贤思想的反哺,对君子之道的践履,转化为一种成人之教。
总之,深度挖掘和阐释以陆九渊民本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并加以扬弃和转化,是体现中华文化主体性和生命力的重要参考系。就陆九渊民本思想的政治向度而言,陆九渊不仅是一位拥有极高心学修养的学者型官员,更重要的是,他成功地将心学理论与政治实践有机统一起来。“从心性到政治”,陆九渊将心学理念始终贯穿于政治实践之中,透露出儒者的仁心、悲悯与济世,为先秦以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注入了新的学术滋养。“本心”的现实使命感如同“横渠四句”滋润心田,莫之能御,激励着后世学人投身于“觉民行道”的事业之中。
参考文献
[1] 何俊.俯仰周旋只事天:陆象山的仕宦生涯.学术界,2024,(12).
[2] 蔡仁厚.宋明理学·南宋篇.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9.
[3] 欧阳祯人.从心性到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4] 冯时.说“民”.古文字研究,2020,(1).
[5] 牟宗三.从陆九渊到刘蕺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
[6] 郭齐勇.中国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7] 单虹泽.陆象山的“主民”思想及其对晚明“觉民行道”的开启.学术探索,2020,(3).
[8] 赵伟.陆九渊门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9] 欧阳祯人.心学史上的一座丰碑:陆象山诞辰880周年纪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
[10] 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